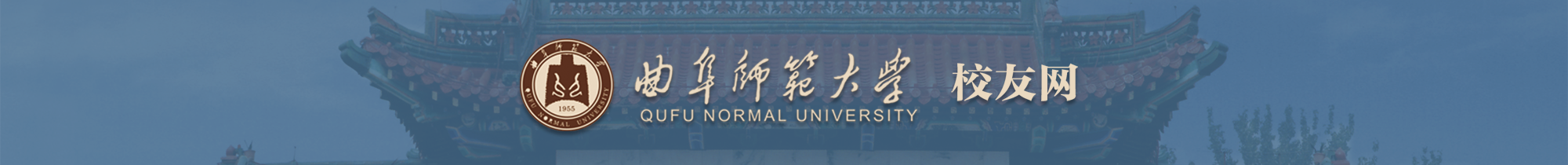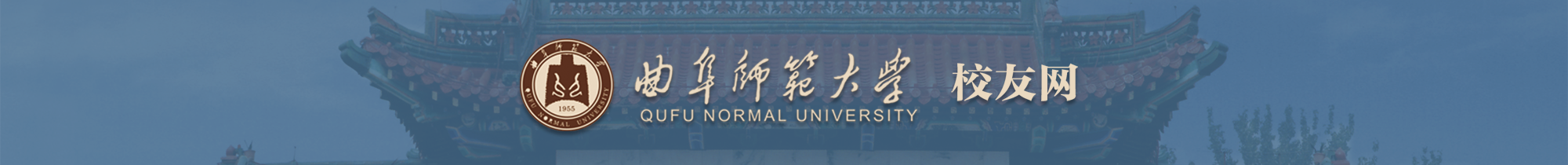引子 我不会画,却拜过山水画家陈我鸿为师,学做人与作文。因愚钝疏懒,学无所成,引为憾事。2002年12月18日,是我鸿师辞世十周年纪念;忆及恩师教诲,念其一生遭际,心中凄怆良久。 我鸿师原名陈金木,字渐陆,此字出自《易经》“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之句;落款他偶称鸿先生或老鸿。1987年秋,曲阜师大同学韩世进跟我谈起美术系的陈我鸿先生,我极慕其画品人品;后有我鸿师的入室弟子王林海、刘继晓到我们中文系听课,课间又说起先生,遂萌生拜访愿望。记得是一个周末,我带了两瓶价廉白酒,拳头大两小包五香花生米,敲开了先生家门。先生头戴紫黑色平顶毡帽,着很笨拙的中山装,黑色棉布鞋,长方脸。个子在一米六左右。操一口南方普通话:“小逄来了!”“逄”字发的是“胖”字的音,“来”字声调拐了个弯。花生米倒在小碟里,白酒倒在小杯里,师徒自日午喝到日落。 我的求学日记上记录着许多与我鸿师交往的点滴。最集中的是1989年4月30日,那天从早9点一直到深夜,在我鸿先生家,一边陪他喝酒,一边听他详谈个人经历。他讲我记,记了30多页。晚上画家杨象宪先生造访,杨先生说:“听听满好,这是陈老师第一次向你公开身世。他轻易不开口。”那天,我鸿先生专门找来《中国地图册》,我对江浙一带的地理不熟,我鸿师讲到一个地方,就在地图上点一下,给我一个直观印象。讲到悲伤处,他的泪光在眼眶里旋动。 剃头匠的儿子 我鸿师1937年农历8月13日生于浙江奉化县亭下村,祖籍浙江嵊县。亭下村依山而居。我鸿师跟我谈时,手捏酒杯仰脖饮下:“那是个好地方。这一带有著名的雪窦寺、千丈崖瀑布、妙高台、三鹰潭等风景名胜。”奉化也是蒋介石的老家,我鸿师家距蒋介石老家溪口很近。蒋介石宣称“下野”时在奉化老家隐居了3个月零4天。并且在溪口与全家过了一个大年夜,这是自其1913年离乡以来36年中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1949年4月25日,迫于战事,蒋介石离开奉化溪口,我鸿师说:“我那年12岁,我跑到雪窦山下,见到逃跑时的蒋介石,他一直说:‘好,好,好'。有逃兵还把帽徽给我作纪念。”说起故乡,我鸿师一脸的幸福感。 我鸿师的父亲是个剃头匠,一生胆小怕事。1950年斗地主,父亲也恨地主,气得发抖。但地主小老婆跪地求饶时,别人让父亲打,父亲说:“我从来没打过人,不会打。”这句话一直深镂在我鸿师的脑海里。我鸿师小时个子很矮,但很喜欢打架。老师的评语是:“野性未改,个性很强。”因出身卑微,常挨欺负,小时经常背着小弟弟玩,小伙伴恶作剧,把辣椒抹到他眼睛里,眼睛辣得睁不开,转悠着掉进水田里,浑身泥巴。但他不哭,更不屈服,我鸿师自称是“牙硬”派。但免不了被父亲痛打一顿。我鸿说,我父亲很有意思,不会打别人,却会打儿子。因为逃学,把砚台掉到地上摔破,也挨过父亲的打。 1955年1月我鸿师在奉化初级师范毕业,因他画得不错,被教育局的一个女干部所欣赏,她也喜欢画,就把我鸿师分到城里,也即新昌县立第一小学任教。我鸿师说:“我不会讲话,一讲就脸红,解放初,小学生年龄在20岁的很多,都比我大。有些学生捣蛋,我教不下去。” 1956年夏,浙江美院第三届附中招生,报名时间已过,我鸿师还是写信报了名。浙江美院附中当年一共招收40名,报名的2000人。他居然榜上有名。3年后保送上了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山水画科只录取了4个学生,他们是李棣生、徐英槐、崔沧日和陈金木(当时我鸿师多用此名)。潘天寿当时是校长,他教画论,陆俨少较画法。陆维钊教古文,我鸿师古文在班里里最好,他从小喜欢古典文学。 上初级师范时,我鸿师爱上了同学王风君。王风君出生在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老家也是奉化,有七亩地。抗战时由上海“避难”到老家,她的家境比我鸿师要好,工商业改造后,还能得到不薄的分红。当时浙江美院大多是“贵族”,而贫农出身的只有陈我鸿,她就资助他,他很喜欢逛旧书店,遇上好书暂时没钱,就先让店伙计保存。《战争与和平》、《宋拓西楼苏帖》、《明原拓石鼓文》就是王风君掏钱给买的。这几本书,一直带在我鸿先生身边,为了生计,该卖的,都卖了,以至于卖血,就是没有卖掉这些书。我鸿师曾对我讲,他跟王风君上学时就相爱,王风君假期回上海,陈我鸿就把照片寄给他,还写了信。但王风君的父亲说他们是小康之家,不能跟剃头匠的儿子联姻。姻缘之线骤然崩断,接起来却花了20多年。 流浪岁月 1963年10月,我鸿师毕业后到浙江省委社教工作团工作,这个社教团就是被定为“枫桥经验”的浙江诸暨枫桥社教工作团,“枫桥经验”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经验。陈我鸿作为一名刚走出浙江美院的大学生,在这里稿社教不只其深浅,结果付出了沉重代价,人生轨迹因此而大变。陈我鸿到工地修水库,工地上诸暨枫桥绛霞村一个女子,长得满漂亮,陈我鸿天天见她,慢慢就好起来。我鸿师对我说:“当时也不去了解,后来别人说她是地主的女儿,我也不管这些,两个人一起去绛霞村看戏。社教队长是浙江大学的,在后面追我,我们就跑。”从此,陈我鸿就带着这个女子杨某(后来草草结婚)开始了流浪生活,他抛弃了一切。趁着夜色,离开诸暨,步行入奉化,一路上住凉亭、庙宇,有时就在草堆桥洞里凑合着过夜。后来一路乞讨到了江西弋阳。我鸿师用手指着地图告诉我:“就是这儿,是江西弋阳的曹溪……”陈我鸿什么也不会,书呆子一个。正可谓力难缚鸡,谋生乏术。他是投奔妻姊的,二姐夫好赌,他不会,就给赌徒们望哨,这样可分点钱糊口。后来,我鸿师觉如此有辱斯文,就操起画笔。有个村庄弄戏台,就让他去画。他还开始用墨铅粉给人画像,死人活人都画。纯粹为了肚子。 我在我鸿师家里见到一个怪条幅:“为腹不为目”,我鸿先生真是饿怕了。他说:“吃亏是福,吃饱更是福。”随着孩子的降生,吃的问题更不好解决。陈我鸿开始卖血,他的体质很弱,医生不给抽,他找了个熟人走后门,一月抽两次,每次300CC,得30块钱。有一次输血回来,头晕,那天是老婆生日,忘记是啥原因了,吃饭的时候。跟老婆抄架,老婆用东西砸到他头上,血流不止。他躺了五六天才恢复。 陈我鸿不通世故,家庭琐事基本不管不问,喝喝酒,看看书,还有抑制不住的是创作冲动。他跟妻子关系没有处好,曾经因为生活上的摩擦而数次自杀。刚结婚时,他买了一条烟给父亲,自己也顺手抽起一支,让妻子发现,妻子在父亲面前动手打了他。陈我鸿觉得有失尊严,抓起调绿色的藤黄,就吞下去。(藤黄有剧毒,相当于水银。)家里人急了。送他到宁波医院,陈我鸿拒绝灌肠。最后抢救过来,花了一百多块钱。1973年,陈我鸿到离家30多里的一个小厂子搞设计,一开始不错,朋友天天请他喝酒,画画也有了大进。有一天,上小学的女儿跟同学吵架,妻子赶到学校去吵,对方孩子的妈妈也去吵,她是陈我鸿朋友的妻子,他觉得很不好,就不想住下去。把家搬到奉化第二陶器厂,干了八个月,夫妻之间又吵,陈我鸿实在受不了,精神彻底崩溃。新结识的朋友看着他很可怜,就劝他忍耐。我鸿师讲到这里,使劲拧紧了眉:“小女儿刚出生,老婆把她丢给我。我想都没想,把孩子扔到雪地里。我到街上买了两瓶最差的高粱酒,到厂医务室,乘大夫不注意,偷了150多片安眠药。把两斤白酒全喝光,吞下所有的安眠药。只觉得天翻地覆地转,十二月大雪天,痛苦极了。在床上一下子跳起来,一下子掉下去。老婆发觉了,跑到医生家里把医生叫来。真可怕!人家说吃上安眠药昏迷,我根本不昏迷。医生对我老婆讲,尽力而为,但没有把握。好歹又活了过来……脱险后,又呆不下去,我只好联系朋友,到山里劈竹子,用竹子做温度计。”他一个人寂寞了,盯着一支秃笔,会小声地吟诵《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温暖的晚景 1978年秋,在奉化,我鸿师跟前妻离婚,他回忆说:“她把我的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明原拓石鼓文》也拿走了,还有毕业文凭。一条破棉被给了我,那是58年我上师范时,父亲给做的。孩子她带走。”一个偶然机会,他从朋友处得知初恋情人王风君仍孑然一身,于是续起旧情,一对有情人终于重牵红线。我鸿师在奉化县城买了间小平房,终于结束了十几年的流浪生活。 我鸿师一直有考研究生的愿望,浙江美院毕业时,他报考李可染的研究生(李可染是黄宾虹的研究生),潘天寿先生和吴弗(加草头)之先生坚持让他留在杭州跟陆俨少先生学,不考研究生。我鸿师回忆道:“我们的系书记是刘苇老太太,她是跟郭沫若、郁达夫一起的油画家倪贻德的夫人。刘苇老太太跟我谈话,说工作以后不许谈恋爱,四十岁以后讨不到老婆找我负责。潘先生也主张谈恋爱应迟一点。可是毕业搞社教,我竟然看上了地主的女儿,唉!”1979年,结束流浪生活的我鸿师又报考研究生,考美术史。考点在奉化,他专业课考了八十上下分,外文不及格,没有录取。朋友吕业翔介绍他到杭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师母王风君放假回到杭州,可巧前妻也来,要求把孩子留下让他抚养。前妻的吵闹,又无法让我鸿师呆下去,于是由自己的一个学生引荐,到宁波工艺美术公司当临时工。 1980年3月,中央发布政策,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重新作为国家干部,奉化老家来了通知,(陈我鸿先生的户口在奉化),后来通知辗转到了宁波工艺美术公司。1981年下半年,我鸿师终于成了干部身份。1984年,画家杨象宪先生路过宁波,拜访我鸿先生。杨先生推荐我鸿师到曲阜师大,1984年我鸿师来到学校试教,1985年秋天正式调到了曲阜师大美术系。那时曲阜师大美术系刚刚从艺术系分离,美术教师匮乏,陈我鸿先生的到来可谓正逢其时。他在绘画技法、美术理论等方面都属上乘。他带着学生上山下乡写生,自己也迎来了创作高峰期。为照顾我鸿师,王风君也办理了内退手续迁来曲阜。陈我鸿的才气和学养使他很快融入曲阜的文化圈内。“孔子研究会”是一个国际性儒学研究机构,会长是孔德懋先生,复出的著名文史学者苏渊雷先生是副会长,苏渊雷被誉为“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曾与数学家苏步青、画家苏昧朔一起并称。“平阳三苏”。苏先生几次到曲阜都会找陈我鸿,陈我鸿就跟研究会的关系很密切。1986年日本静岗县书道团访问曲阜,又值新加坡总理内阁咨政李光耀曲阜祭孔,陈我鸿都被邀请参加。应该说,在曲阜师大的7年,是我鸿师生活上最好的时期,也是他艺术上发挥最好的时期,可惜正当他向着艺术的最高峰攀登的时候,竟然在1992年12月18日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年仅56岁。 敬慕贤哲 谈到对画的兴趣,我鸿师说:“我很小的时侯,父亲在家里供着菩萨像,别人以为菩萨放在家里不好,父亲就打碎了,我就大哭。父亲画个螃蟹给我看。我画画的兴趣就来了。邻家有连环画一本一本的,那时我认为画得很好,就赖着不给人家了,闹到别人来讨。”认识我鸿师的人,都说他天生是个画家。我鸿师说:“没有老师的指点,我一事无成。” 影响陈我鸿最大的,是潘天寿先生和陆俨少先生。潘先生教画论,在第一堂课,潘天寿讲了两点:一、你们要集中精力,埋头学画。要决心一辈子献身艺术。二、你们要不存偏见,博采众长。不要以学像我为满足,要着眼于创造。要记住:艺术的重复等于零!这些陈我鸿一直铭记在心。陈我鸿说,自己在困境中,正准备消沉的时候,常常想起潘先生的身世,活下去的力量马上就传遍了周身。潘天寿出身很贫苦,7 岁时父亲死了,他在农村做过农活,下过田,车水、砍柴都干过。他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师范最有名的人叫李叔同,从日本回来,修养全面,是他们的教师。后潘到上海供职于刘海粟的美专。潘到上海美专后,学校才设立了国画系,原来该校是以油画为主。潘天寿在上海主要求师于吴昌硕,他经常利用教书空余到吴昌硕处,听他指点。吴昌硕很器重他。潘天寿为人正直,生活俭朴。他也很少卖画,一味搞学问和画画,他在艺术上非常严谨。浙派画家重骨气,其作品一般都是剑拔弩张,锋芒毕露。但潘天寿笔墨有力度而内涵,他有个图章,自嘲“一味霸悍”。潘天寿擅画写意花鸟和山水,远师徐渭、朱耷、石涛等人,近法吴昌硕;作画主张“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见识,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有所成就”。布局敢于造险,又破险。我问陈我鸿先生何为破险?他拿过《潘天寿画集》,指着一幅画说:“你看这块石头,尽量往四面扩张,石头都快出了画边了,但是他又用流水破掉。有时他会用个动物破掉,寥寥几根线,经得住推敲,其功力来自书法。潘先生主要写隶书,有时又写篆书,题画非常考究,题画是他构图的一部分。他的行书也写得非常潇洒,他的线主要得力于书法,他写字的时间多于画画……”一说到潘先生,我鸿师就收不住嘴。画累了,我鸿师就翻看《潘天寿美术文集》。 陈我鸿跟我讲了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1957年潘先生来到浙美,当时浙江美院山水画系主任是吴弗(加草头)之先生。我鸿师说:“吴先生一开始看不起潘先生,说,这个乡巴佬能画画吗?就问:‘潘先生你画张画看看。'潘天寿先生是农民样子,很忠厚,不大会讲话。潘先生搔头皮,然后几笔下来,只见笔墨浓重豪放,色彩单纯,气势雄强。吴先生一下子佩服了,跟着我们叫老师。文革时,学生斗潘先生,造反派让潘先生坐着,吴先生可以坐着。吴先生火了:‘我老师站着,我能坐么?!让我老师坐。'”潘先生跟吴先生后来成了莫逆之交。潘先生曾对我鸿师说过:“找吴先生画画,你可要当心,看他画到差不多时,马上抽掉,否则就画坏了,吴先生收不住自己。”我鸿师说,我的老师都是人瑞,能跟他们学,是三生有幸。 “沉住气,慢慢来。一笔一笔画。”我鸿师经常说这句话,他还说,因为坐不住,很容易走马观花,这对自己的修养很不好。画画跟说话、写作一样都要保持一贯性,也就是要“死心眼”,不要寐着良心说、画、写。他说这些都是从陆俨少先生那里学来,又经过自己摸索得来的经验。1962年,五十四岁的陆俨少受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先生邀请,赴杭州任教大学四年级山水课,陈我鸿从此开始跟陆先生习画。他回忆说,陆先生的山水画法,往往是先由局部下笔,然后生发,最后成局。一反王原祁以至黄宾虹都是由大到小,先定位置,逐渐构搭的画法,由小到大,笔笔生发。陆先生常常讲:“我是画到哪里是哪里。”这种“画到哪里是哪”之法其实正式建立在其独特的“笔墨生发”的画学思想之上。从陆先生的山水画的整个框架结构来说,以浓为骨架,由浓入淡,由润至燥,常以生辣的几笔浓墨作起首,然后以干笔淡墨皴擦。如果将先有一画作为“启”,那么后一画便为“随”。作为先导的“启”笔是主,而后继的“随”则必然是根据前一笔的或大或小,或浓或淡,或燥或润,或疾或缓进行补笔。一笔接一笔,一笔复一笔,如此反复生发。如波连潮涌,笔笔紧跟,往复更叠,不能自止。陆先生作画从不打草稿,虽巨幅经营,也只大体安排位置,然后下笔,不受拘束,笔随神行,奇思壮采,合沓而来。我鸿师非常推崇陆俨少先生的艺术观,比如:“窃以为学画而不读书,定会缺少营养,流于贫瘠,而且意境不高,匪特不能撰文题画,见其寒俭也。”“我自己有一个比例,即十分功夫: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有人把看画也叫读画,画读得多了,胸中有数十幅好画,默记下来,眼睛一闭,如在目前,时时存想,加以训练,不愁没有传统。”我与我鸿师接触,见他什么书都爱读,他喜欢读欧文·斯通的传记,喜欢苏东坡的诗词文和书法。喜欢哈代的小说(尤其喜欢他的《卡斯特市长》)有一次,我专门给他买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他大为欢喜。当然,读的最多的是名画家的画作,我从他那里知道了石涛、八大山人、赵子昂、方从义、董其昌等等。 顾坤伯也是陈我鸿的恩师,反右倾的时候,有人说:“光领工资,不干活的,比如胖得像猪一样的顾坤伯先生。”顾先生气得鼻子都横起来,竟气病了。管事的不让他到病房,就在走廊上。我鸿师说顾先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他上课,宛若春风坐帐,一片祥和。他主张:“画艺须师造化,又师古人,融合为循环式圆圈,天人相接,自达妙境”。迄今不忘。陈我鸿对顾先生的笔墨非常崇拜,他为自己上大学时没有化更多的力气钻研顾先生笔墨而后悔不已。他认为中国山水画这跟线,到了顾先生手里是正宗,尤其对顾先生的用色推崇备至。比如将唐宋金碧山水的浓艳与元明浅绛山水的清淡融为一体,青绿设色独具风格,给人以秀丽清新之感。对此,陈我鸿心向往之。顾先生从前贤处得笔墨,得意气;从造化处得灵秀,得天籁的从艺之法;顾老苍浑中有清润,沉着中见秀逸的画风也深深感染着陈我鸿。我鸿师还向我介绍了补白大王郑逸梅写的《吸烟肇祸的一斑》,其中写到:“无锡名画家顾坤伯;号二泉居士,从陈迦庵、吴观岱游,作山水苍浑入古。一度和我同事苏州旅沪公学,他教图画,循循善诱,成绩斐然。后来他自办奇峰国画学校,金针度世,门弟子蔚然称盛。他也是吸卷烟成癖的,有一次,临睡吸烟,烟烬焚及被窝,及灼肤生痛,才张目醒来,急起扑灭,那被窝已毁去半条,他被灼患病,不久逝世。卷烟为害如此,凡嗜吸的。能不引以为戒吗!”我鸿师一边说,一边还抽烟,他说,我这也是学顾先生啊,说毕大笑。 我鸿师让人景仰的是他景慕贤哲,真正是见贤思齐。曲阜师大的陶愚川教授,埋头数十年,孤身完成巨著《中国教育史》,把稿费全部捐给社会。他是学问大家,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美国和日本。我鸿师对我说:“要做这样的人,他的人品很高。有一次开个什么会,陶先生拄着个拐杖,咯哒咯哒慢慢走,后面跟着个小轿车,这是什么事呢?原来是司机师傅去接他,他说:‘我坐不惯',有意思的老头儿。”我鸿师对陶先生的学识和人格极为羡慕。 画与酒 陈我鸿大学毕业时,和三个同学去求潘先生画,潘先生好好好地应着,喝点酒,四张画从十点一直画到夜里三点。陈我鸿也跟潘先生一样,有朋友求画,喝点酒,一直画,有时竟然画到天亮。他说:“画应酬画,不能应付的。” 1989年元月14日晚,我到我鸿师家去。他正在给王林海写画展的介绍。画案上放着白瓷酒盅,酒瓶。三个小碟子,里面盛的分别是干巴小鱼,豆芽和炒白菜。我鸿师一见我,就高兴地拍我的肩膀,一手捏着酒杯,让我也喝,一边叫小女儿给我泡茶。 我鸿师说王林海画展是沙孟海题的字,沙孟海当过蒋介石的秘书啊,那字写得真好啊,绝了。我从未见我鸿师这样推崇一个艺术家。他喝一口,说:“昨天一夜没睡觉,朋友要画,我只好连夜赶,脑子里有点糊涂了。”他外边套一个黑布坎肩,扣子也是黑的,里面的黑衬衣有一个领子露在了外面,他也不顾。只顾喝和画。 那晚上我鸿师谈到了画与酒,他说:“画画必得喝酒,不能太理智,迷迷糊糊的,才能画出气,画出境界来。酒是好东西啊。”他还说,继晓的画还是太理智,我看他也需要喝点酒。 陈我鸿先生说,原来他有好多珍品,收藏价值很高。有个朋友是教书法的,每次拿一瓶酒去拜访他,让他喝,一喝醉,那个朋友就向他讨,陈我鸿就让他随便拿,结果好多就被拿走,其中有蔡元培先生的亲笔扇面。等他醒来,后悔不迭,但已无法挽回。 据刘继晓回忆,在曲阜师大时,曲阜城里有个扶兴和笔庄,老板人称龚麻子,陈我鸿经常光顾,一进门就喝酒,喝到微醉,龚麻子就准备好纸笔砚墨,请陈我鸿画,这样画了不少。有一次,龚麻子拿出清朝的纸,请陈我鸿去求陆俨少先生的画,陈我鸿已经喝到半醉,连连说好好好,居然求到了。 我鸿师的几乎所有的画都是醉后作的。1989年6月19日,我到我鸿师家,见他家客厅兼卧室的南墙上挂着《飞香走红满天春》。画面上方是枯枝斜伸、红花点点,下方是诗人李贺骑着快马飞奔,蹄踏落红。提款是“丙寅端阳老鸿狂醉写长吉诗意。我鸿师说,那是自己刚从南方搬到曲阜师大,五月端午节,大醉后画的,那时心情很好,比较得意。他说:“李贺不错,诗的意象阴森可怖。人谓诗鬼。27岁就死了。真可惜,是大天才。毛主席也很喜欢他,‘雄鸡一唱天下白'就是借李贺的。”我鸿师跟我讲的时候,也没有离开酒杯,当然我也陪他喝了一点。 我鸿师作有《酒德颂》图,画面上的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席地而坐,右手擎着酒杯,身前放着酒葫芦。画上部是《酒德颂的全文:“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ke(木盍)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注],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我以为〈酒德颂〉简直就是我鸿师的自白。 我鸿师曾经画过《幽讨先生牧羊图》,师母说,为画这幅画,他哭了两天,边喝边哭边画。幽讨先生是他的忘年交,奉化董村人,一生好读书,能背诵〈史记〉,曾任国民党中央要员,后蒋介石逃到台湾,幽讨先生无意政事,留在乡里以牧羊为生,读书为乐。陈我鸿在画的题跋中写到:“八十老翁,胃纳不减,恒餐大米四两。曾与余斗酒,余大醉而卧,二时方醒。先生呵呵大唉(疑为笑—阶按),尚手不释杯……”陈我鸿跟幽讨先生饮酒是在文革时期。这幅画是为纪念幽讨先生十周年而作的。师母讲,幽讨先生有一次给陈我鸿看相,说他36岁有一劫,因有贵人相助而幸免。但逃不过56岁大劫。幽讨先生的玩笑话,陈我鸿竟然很相信。他说反正怎么仔细活都会是是56岁,干脆什么也不在乎,饮酒必醉,病不求医。谁想幽讨先生一语成谶,我鸿师竟然就是56岁上故去,令人伤悲。师母说,如果我鸿师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不至于这么早就离开人世。 师与徒 我鸿师回忆说:“潘先生名气很大。有个农村小伙子喜欢画画,来拜见潘先生,先生正忙着在画室作画。师母怕他太累了,就对小伙子说,先生不在,潘先生在里面听到了,对着师母发火:‘我在就在,我不在就不在,不能说谎话。'”我鸿师对学生也如此。刘继晓当时到曲阜师大进修生物,因喜欢画画,就到美术系求教,有人推荐了陈我鸿先生。刘继晓带着一个老大的西瓜去拜师,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我鸿师一点点地给他启蒙,给他推荐了一些名作,让他临摹,后来给他修改习作,领他去写生,刘继晓越画越出息。 画家尹舒拉也是陈我鸿先生的学生,他在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谈到了跟我鸿师相识的经过:“1972年初,我参加青田县的一个美术加工会。因为,我有一幅作品要通过这个加工会加工,然后逐级上送,去参加‘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我的作品叫《田园春色》……我记得当时大约有三十来幅作品参加加工会,而上送的只有五幅。我作为一个乡下进城的小毛孩,根本不知道自己这幅作品有无可能入选,心里只是将一个月的加工会,当作一种高级享受来对待。一天上午,来了一批画帘厂的大师傅,看样子是有组织来的,他们鱼贯而入逐个看人逐副幅看画。当他们来到我身后时,我觉得后脑一阵发麻。来看画的人,大多与加工会里人熟悉,他们话长话短好生热闹。只有一位中等身材沉默寡言者站在我的画前看了许久,问我是哪里人,跟谁学画等等,并说有空可以到他画室去看看。这个人自我介绍叫陈我鸿,并向我要了半张宣纸。县画帘厂在青田人的心目里,是‘美术大师'云集的地方,如果能去画帘厂画室去看画师作画,真可谓求之不得。当天下午上班时间未到,我就到了画帘厂画室门口,少许,陈我鸿来了。他对我点点头,我就尾随进去。他说他长久未画宣纸画了,水分控制不好,边说边将他上午从我这里拿去的宣纸画出的画拿给我看。画面上一些乱石和鸡毛一样的松树,石与树的样子都很古怪。当时我怀疑水分未干,用手去触摸,方才知道是干的。我觉得好生奇怪,陈我鸿说这种纸很好,只是他十来年未画画,画得不好。我要他上些颜色看看,他顺手蘸了些赭石和花青,和着墨一笔一笔往纸上画,并告诉我山水画的用色要沉着,不能有火气。这些都是我从未听过的词汇。我问他怎样才能学好山水画,他说多看好的画,提高眼界。我问怎样才算好的画?他说要多读画论。并说光会画,不通画论,画得再好也是‘画匠'。”尹舒拉跟陈我鸿就这样相识,我鸿师从最基本的东西跟一个初学者讲解,尹舒拉也没有辜负我鸿师的期望。师徒亦师亦友,从相识到相知到深知,成就了一段画坛佳话。 记得那年,我刚照完毕业照,整理行李准备到昌潍师专供职。我鸿师敲开了我的宿舍门。手里拿着他的赠画。题跋是“春阶仁弟一笑,我鸿醉写”。我看到整幅画乍一看很不规则,好像是糊涂乱抹,但笔笔有“来头”,狂放中带着一种落寞,率意洒脱的用笔背后,让我感觉是满纸酒气。画的前景是两个小草屋,一抹淡红的土墙;中景是一组荒寒的枯枝,枯枝上有几枝寒鸦在盘旋。远景是壁立的雪山。引我联想到放荡不羁的孤独的行者。画的压角章是“鸿飞哪复计东西”六个字。我鸿师、非常喜欢苏东坡的诗句,有时喝上酒就面对了我吟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画画的心态 我在《陈我鸿画册》上看到一幅《温溪小景》,画面主景是一株榕树,灰蒙蒙的调子,树边有一座小庙。左上角从树丛里撑出一只小舟,撑舟者是一位头戴斗笠上着红衣下着绿裤的女子,显得颇有生气。可惜这幅画上面有三处油污。舒拉先生回忆到:“陈我鸿在青田画帘厂时,每月的工资,只有二十七元,当时一家四口生活十分拮据。有一次,我和他一同路过一个饮食店,门口正好在炸油条,且不收粮票。我掏钱买了两根。因为买的人很多,油条起锅就让人抢去。我怕烫手,没敢拿,陈我鸿见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灰不溜秋的纸,为我抢了滚烫的油条。回到画帘厂地下室,我和他一家好好地食了一顿美餐。饭后,才发现刚才包油条的指是一幅画。我随手拣起,陈我鸿要夺去撕。由于我手脚快,这幅画一直保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