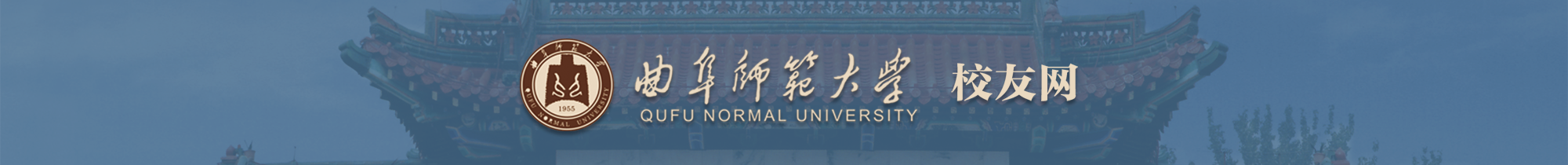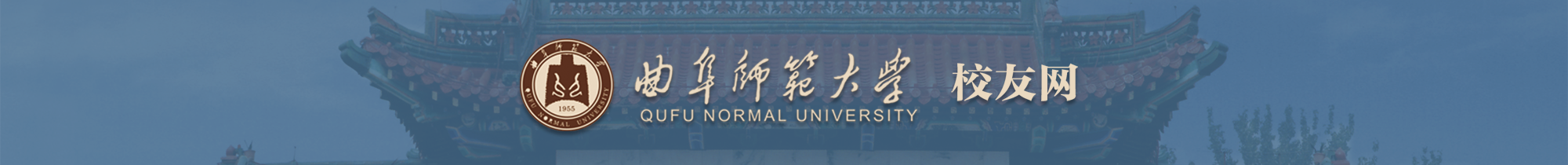2010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刘健的文章———《现在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下称“刘文”)。文章发表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国内许多家报刊杂志予以转载。文章以新颖的视角向读者诠释了我校陶愚川、庄上峰、包备五和李毅夫四位教授的另类人生,让人读来耳目一新,感慨良多。 我与这四位先生均有接触,也曾经走近过他们的生活(注:本段内容摘自拙文《我所认识的“怪教授”陶愚川先生》,《齐鲁晚报》2012/4/23)。在此,我想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怪教授” 庄上峰先生。 庄上峰先生1909年2月生于山东省莒县大店村。其父庄陔兰是清末翰林,曾任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塾师。1946年病逝,葬于曲阜孔林,其墓犹存,为孔林唯一外姓墓葬,可见孔德成重教尊师之谊。 庄先生1930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同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注册部主任。1945年2月参加革命,曾任八路军滨海军区参议、山东军区交际处教员。后来又在山东人民政府政治干校、华东建设大学、华东军区卫生部、白求恩医学院、山东医学院工作或任教。1950年至1962年在山东省图书馆工作。1962年8月调至曲阜师范学院(今曲阜师范大学)从事外语教学工作,后在该校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1985年3月18日在青岛病逝,享年76岁。 1963年我从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任教,当时先生正教二年级的“精读课”。有一天我去他班听课,发现先生讲课的风格与众不同。他说话慢条斯理,从不高声。令我十分好奇的是,他讲课时不是自己写例句,而是叫一位学习好的学生站在黑板前替他写。 庄先生成长于诗书世家,待人向来彬彬有礼。记得刚来曲阜师范学院时,我还是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但先生每次见面总称呼我“曹老师”。当时我十分不好意思,觉得这个称呼有点承受不起。我让他改叫我“小曹”,但无济于事,先生终不改口。 庄先生知情达理、礼貌待人还有一例为证。我不曾见先生带过帽子,即使是寒冬,他也总是把头梳得一丝不乱。上课时他要求学生把帽子摘下来,说这是礼貌,表示对人尊重。这不禁让我想起金岳霖先生。“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带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汪曾祺著《草木春秋》P.58)。我想,关于帽子的礼仪,出身诗书世家的庄先生是了然于胸的。 庄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受过高等教育,又供职于山东图书馆长达12年之久,先生一生饱读经书,学富五车。古今中外的名人轶事,历代宫廷里的趣闻,先生都了如指掌。他给我讲过江青的往事,也讲过“印度圣雄”甘地和英国诗人王尔德的故事,就连“扒灰”(意思是“老公公偷情儿媳”)这样的典故他也能信口娓娓道来,讲完呵呵一笑。 庄先生还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老者。1980年我翻译了一本三万字的儿童读物《伊梅尔与侦探》,想找出版社出版。我当时毫无关系,没有门路。于是我想到了庄先生,请他帮忙。听了我的诉求之后,先生二话没说,立刻修书他的好友、新疆人民出版社的陈之任先生,请他帮忙。现在想起此事,我都非常感谢这位热心肠的庄先生。 然而,通过20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也深感庄先生确实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哲学,即人们常说的“怪教授”遗风。 “刘文”也写道:“曲阜师大的老师说:‘你要是早一两年到我们学校采访,还能见到一位比陶愚川教授还古怪的庄上峰教授。’”那么,庄上峰教授到底有多古怪呢?在此,我愿以拙笔实言记述我所认识的“怪教授”庄上峰先生。 当代“庄子” 通过20多年的接触,我深感先生的个人修养已达到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高度。我从来没有见先生发过火,也没见他悲愁过。遇事他总是心静如水,一副安之若素的淡定心态。庄先生有一句名言:“甘苦都能受,升沉总不惊”。因此,“文革”时对他白天黑夜地轮番批斗,他都毫无悲观沮丧之感。后来我问他:“庄老师,学生批斗你时,你怎么不难过呢?”他对我说:“法国一位哲学家说过,在那种情况下,你不要把他们看作正常人,你应该把它们当成疯子。曹老师,你怎么能跟疯子一般见识呢?”说罢哈哈一笑。 是啊,人生在世,哪能一帆风顺,俗话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当人遇到困境时,要“弯得下腰……要处事低调,学会忍耐。宁折不弯,固然值得赞美,但没有意义的粉身碎骨却令人扼腕。弯腰是一种姿态,是为了更好地挺起自己的脊梁;弯腰是一种风范,是为了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韩信选择弯腰,因而成就大汉400多年的基业;司马迁选择弯腰,因而书写流传青史的绝唱。青松因弯腰而坚强美丽,稻谷因弯腰而成熟厚重。弯得下腰,才可能写出诗情画意的人生篇章”(《人生四得》韩冬/文)。 笔者曾读过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及他“文革”中受到非人的待遇却能活下来的原因。他说,我是活得不要脸,所以才能活下来,而老舍先生太要脸了,所以没能活下来。吕先生和庄先生等学者的话语虽然朴实,但却蕴含着非凡的哲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庄先生向来无忧无虑,遇事(即使天大之事)均能做到泰然处之。1974年夏,有一天我们在教研室讨论编教材的事。休息时他对我们说:“丁云(他的夫人)昨天在医院里又吐了半盆血,”说罢便哈哈大笑。曾记否,古代有庄子“鼓盆而歌”(注:该典故出自《庄子·至乐篇》,说的是“庄子的妻子死了,来吊丧的人看见庄子蓬头赤足坐在棺材上敲着一只破瓦盆,一边敲打还一边唱着歌。”),现代有庄先生说妻子在医院大吐血时的“哈哈大笑”,何其相似乃尔。庄先生真可谓是一个活脱脱的当代“庄子”。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身上。大师的母亲去世后,“葬礼上,全家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而不是传统的白衣披麻戴孝;最让人侧目的是,李叔同在葬礼上边弹钢琴,边唱悼歌。在世人的不解中,25岁的李叔同用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感怀母亲的命运,也发泄着对妻妾制度的不满”(摘自2013-7-12的《每周文摘》)。 从庄子到庄上峰先生再到弘一大师李叔同,这些修养脱俗之人的不同凡人之举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庄先生的学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人突然造访先生家并严厉地呵斥道:“ZhuangShangfeng,we’llshootyou!”(庄上峰,我们现在枪毙你)。先生会毫不犹豫地说:“Let’s go.”(走吧!)他绝对不会问为什么。这虽然是笑话,但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庄先生与众不同的秉性和处事哲学。 《雷霆时代》 “刘文”还写道:“庄先生述而不作,不曾有学术专著流传。但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去世后,学校整理其遗物,竟发现了一部长篇小说手稿,名《雷霆时代》”。 我与先生相处20多年,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写作《雷霆时代》的事,这真是应了那句名言“真人不露相”,同时又透出他独有的不显山露水的高贵品质。 该书于1985年6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共297页。我至今也没见过这本书,我校的老师也无一人读过它,就连我校图书馆也无此书,真是“怪”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书“极端写实地描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老同事们的生活———闻一多如何追班里的女学生,以及梁实秋、老舍、游国恩等教授如何如何,稍加揣度全都能对上号。因为太写实了,出版社不敢原样照出,删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就意思不大了”(摘自“刘文”)。 那么,庄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自传体小说呢?或许他在该书中写的“自序”能解答这个问题。他写道: 一本小说,饥不能以为食,渴不能以为饮,有什么用处呢?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成为世界历史上的转折点。那场战争是“人肉磨”,有时一师人只剩六、七个人。在一个战死的红军尸体的衣服口袋中发现的不是日记,也不是相集贴,而是一部小说。这本小说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部小说竟有这么大的力量。它能大大地鼓舞士气。它能使一个战士为了苏联的存在与安全、为了保卫世界人民免受德国法西斯的奴役,而甘心情愿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写的这本小说《雷霆时代》,焉能与伟大的杰作《战争与和平》相比! 但我的小小愿望是:当代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能够从这本小书中吸取、哪怕是一点点益处。“管窥蠡测”。愚者千虑,可有一得。把这本小书当作一得之见的刍议吧。《雷霆时代》不是只供读者消遣而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