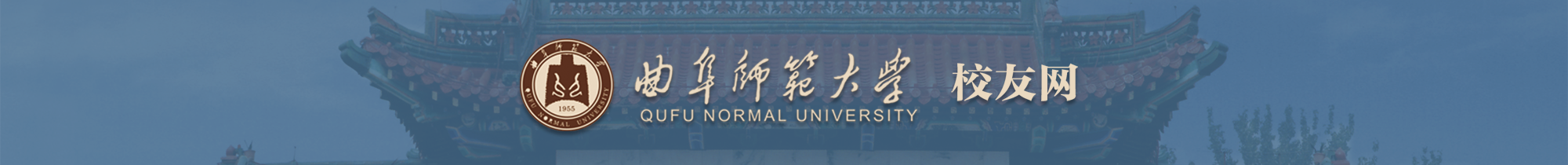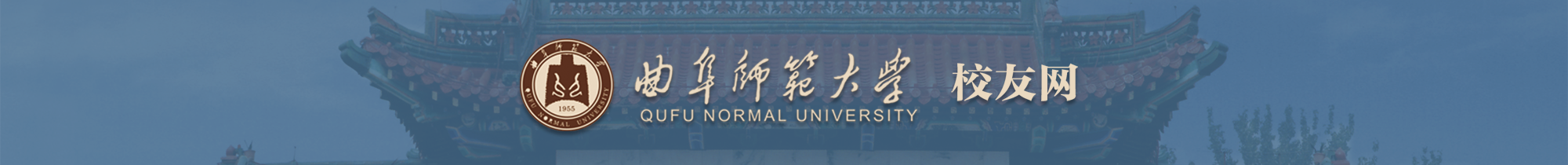在曲师四年大学的历程中,我最怀念的是中文系那几位老师,在这些教过我和没教过我的老师中,有的还健在,有的已白发苍苍,有的调走了,还有的已经去世了,再也见不到了。 我最早接触到的老师是系书记范海风,既听过他的党课,也当面接受过他的批评教育。范书记很朴素,如果在路上而不是在大学里,我会把他当作一个田间老农。他个不高,短发,圆脸,眉头层层皱纹,穿一身粗布或灰或黑的衣服。他说话的音质很特别,不像好多男性固有的粗犷的话音,但又不是公鸭嗓子,说话音质比较细,却很响亮。他给我们上党课,也不是直白地向我们灌输大道理,而是和风细雨地与我们谈心,有时还幽默一把,逗得我们发笑。毕业若干年之后,有一次学校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一见面,他竟然叫出我的名字,令我油然而生敬意。后来不断看到他在校报上发表的古体诗词,才知道范老师古典文学造诣颇深。今年再见他时,不是在西联三老教室里,而是在文学院办公楼前,同学们在栽纪念树的时候。他正好赶早市回家路上,买了一塑料袋蔬菜,有大葱,两截藕,土豆和白菜,还有两条小草鱼,都不大,至多三两重。遇见自己的学生,还是不忘幽默一把,对围着他说话的几个同学说:“怎么样,我买的这些小菜,中午招待你们可以吧?”范老师的幽默和厚道可见一斑。与范书记搭班的是聂建军主任,他的厚道更是广为称道。 前年有同学通知我,说聂建军老师病故了,要去参加聂老师的追悼会。在奥体中心东边,有一个莲花山殡仪馆,聂建军老师的追悼会在那里举行。当我去的时候,七七级的几个老大哥老大姐都已到了,我认识的有刘大星、羊丹娅、樊龙等。我是与张济民同学一块去的,不一会儿,张士新、孔繁熙、王少华等同学也都赶来了。聂建军老师的追悼会很简朴,不收礼金,不要花圈。追悼会开始后,每人在门口拿一朵鲜花,向敬爱的聂老师三鞠躬,然后献花,与聂老师的亲属一一握手。在向聂老师遗像鞠躬时,我就憋不住感情想哭。告别出来,想起在母校时,聂建军老师对我的教诲,忍不住泪流满面。前几年听说聂老师病了,我去看他时,还满有精神的,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他老人家已经去了,就像佛祖身坐莲花而羽化。 我总是将聂老师与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东政委挂号,他俩长得的确太像了:都是高高的身材,黑黑的脸庞,眼睛陷在深坑里,眼大而有神,说话时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聂老师担任系主任很多年,他主讲选修课――经典著作文论。平时大量工作是组织教学,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和学生的思想工作。有时候学生与老师之间发生争执和矛盾,都是他出面调解和处理。他对学生有时很严,比父亲还严;有时他对学生很慈,比慈母还慈。因此,我对聂老师的印象,就是“严父慈母”。他是真正把学生当作自己亲生孩子来对待的。 最让我萦记于怀的一件事是,在即将毕业时,我听说79级有20多个到省直机关工作的名额,却没有我。我气愤地跑到聂老师家去找他,他正端着一碗大米饭在吃饭。我说聂主任你先吃饭,饭后我再向您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放下碗筷说:“你先说吧,饭是天天吃,不急。”于是我谈了自己的想法,那时候我光顾着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理由,说话有点罗嗦。聂老师打断我的话说:“系里我们几个老师对你看法一直挺好,对你在学校四年的表现是肯定的,每天早晨带着同学们出早操多不容易啊。我现在答复你的是,满足你的愿望,到省直机关工作,至于哪个机关,你就不要问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透露。令我愧疚的是,因为我的罗嗦,使聂老师没有吃好那顿饭。 后来,中文系改成文学院,聂老师由系主任升为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由于两地遥远,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很少联系。有一次邓承奇老师来济办事,王凤胜副部长请他吃饭,我去作陪,专门打听了聂主任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校时,邓承奇老师是系里的副主任,也教我们经典著作文论。二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在做人上,还是在做学问上。聂老师是研究灵感的权威,以致于前些年我在撰写谈灵感的文章时,想起聂老师给我们做过一场学术研究的报告,即《灵感是怎样发生的》。聂老师的那篇报告概括为“灵感偶然得之,全赖平时积累”。我在自己的文章《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师承了聂老师的观点:所谓灵感,指的是人们在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中因偶然机遇而疑窦顿开,思路贯通,获得意外创造成果的一种心理现象。灵感是文学创作的发动机,是创造性思维的源泉,灵感是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它既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神的启示”,也不像机械唯物论所说的是一种莫须有的臆造。灵感的实质是长期社会实践与艺术积累的偶然反映。 我在评论界建立的影响,一多半来自聂建军老师和马国雄老师的教诲。马老师长相类似余秋雨,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背有点陀。他给我们主讲《文学概论》。自从我毕业后,一次也没见过马国雄老师。后来听说他调到镇江师范学院了,他的老家是江苏省扬州市的。我在第一学年听他的文学理论课,由于马老师浓重的南方口音,多半是听不懂的,只好课后加大温习的力度。佛祖说, 没有人是因为偶然进入我们的生命,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如今,我想再一次拜见我生命中遇见的老师,一个在天堂,一个在遥远的南方,怎么不令人痛心和牵挂? 中文系有许多大师级的教授,比如编写《汉语大辞典》的谷辅林教授,研究鲁迅的专家魏绍馨教授,研究蒲松龄的徐振贵教授,研究古典文学的王怀让、张元勋教授,研究当代文学的孟蒙教授,教我们写作课的张念穰、任跃云教授,研究明清小说的戴胜兰教授。而且戴胜兰教授是从山大留下来的教授,与山大的萧涤非和袁世硕教授过去都是同事,戴老师还是全国六、七届人大的代表,在国内享有盛名。我想,大学之谓,不在于校园有多么漂亮,而在于是否有大师级的教授。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见过的那些老教授,与曲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没有啥区别,都很朴素,都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越是大师级的老教授,就越是没有架子。 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与魏绍馨老师的接触,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庆幸。我与其他同学有所不同,我不是从高中毕业直接考大学的,我是当过五年兵回乡教民办之后又考上大学的,25岁上大学已经是大龄学生了,到毕业时就有29岁了。家中父母很着急,恋爱问题摆在面前,可是那时我还真的不懂爱情。几位老师都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郭术敏老师知道后,就约我去他家吃饭,郭老师包的荠菜水饺,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的水饺。郭老师满面笑容地规劝我说:“学校不准谈恋爱是对的,在校期间就要好好学习,毕业之后对象好找。”他还告诉我,魏老师和张老师很关心我,抽时间你去拜访一下。我依照郭老师的意见去拜访了魏绍馨老师的家,才知道教我们汉语拼音的张之静老师与魏教授是夫妻。两位老师问寒问暖,说曲阜城内有一户人家,女孩虽然不是大家闺秀,但还算说得过去,知书达礼的。在确定我同意见面之后,张之静老师摸起电话就联系,定好日子去城里见面。我与那女孩子只见了一面,后来毕业实习很忙,就没再见面。但是,不管怎么样,魏老师和张老师那份苦心令我终生难忘。张老师教过我现代汉语,主要是汉语拼音,词与词组那部分是赵老师教我的。张老师还在越南教过学,她的经历肯定是不平凡的。她就像我的母亲,在教给知识的同时,还关心我的个人婚姻大事,不是母亲般的胸怀,怎么能够做到? 二00九年回母校聚会,我又去看望魏老师,明显地感觉魏老师老了,说话语速慢了,动作也迟缓。张之静老师从学校食堂开水炉打了两瓶开水,一手提一个暖瓶回家。在微风吹拂之下,张老师满头银白色的头发闪闪发光。岁月如刻刀,两位老师都满面苍桑已近古稀,我只有欷嘘不已。 教汉语词与词组的赵老师,毕业之后我又见过若干次。记得在九十年代初, 谷汉民老师由曲阜师范大学调到山东师范大学任校长,在刘耀庚同学组织的欢迎宴会上,我和部分同学参加。那个酒店在历山路东仓附近,我见到敬爱的谷汉民老师和他夫人赵老师,真是令人高兴。我与两位恩师的亲近是必然的,因为谷老师在录取时收了我的档案。在酒桌上,谷老师谈起这段往事,还是记忆犹新。我总是将谷老师比作列宁,一样的个头,一样的气派,一样的秃顶而且前额突出,人家说从年轻时就败顶的人特别聪明,所谓“聪明透顶”,此言是也。谷老师没给我教过课,但是,我与他一直没断了联系。赵老师从曲阜往济南搬家时,我还去看望过。 曲阜师范大学还有许多老教授,比如张元勋教授、孟蒙教授等,都是有故事的老教授。我在其它文章中专门写过这两位老教授,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写去。 三十年一恍而过,岁月苍老了我的许多恩师,却磨灭不了我对他们的记忆。佛祖说: 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在对的时刻遇到对的人,受到那样的教育。因此,我的故事仿佛都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当进入新的世纪,经济高速发展将人们推进金钱社会时,我环顾四周,再寻找母校时光那种纯洁的师生关系,却因找不到而茫然失措并黯然神伤。因此,有时候我总是怀有深深的伤感,就像孔子怀念周代的理想社会而所处时代却天下大乱秩序不复存在而伤感。这种伤感不仅来自社会,当然也来自我对人生的失望。可是,人生的路还要走下去。我将牢记恩师的教导,继续书写我的故事,走好后半生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