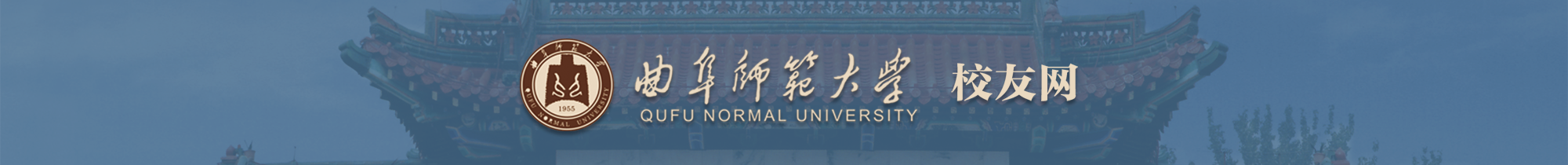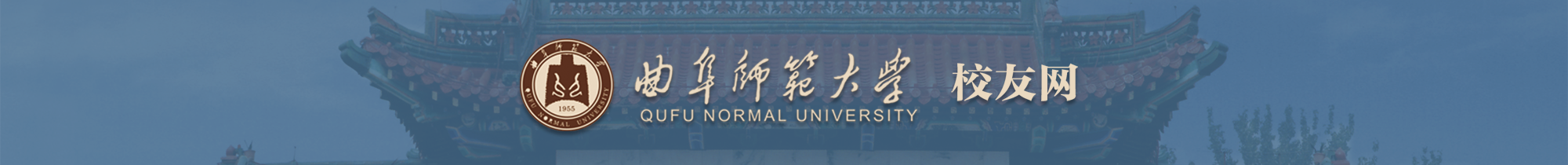与“园”有关的词,有“校园”“家园”“田园”“园林”等词,以一园字立名,而又能体现诸词内涵的,当有“曲园”一词。 曲园,是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子对母校的称谓,简单的两个音节,承载着无限依恋眷顾之情。时空之越阔远,依恋眷顾之情也就越深。 我从曲园毕业,至今忆历十三载。这当中尘海翻伏,教务繁忙,没有闲暇能重沐母校惠泽,只能从校友录中零星了解母校的一些人事,还有母校沧桑变化的图景。残缺之为美,距离之为美,说不清有多少美学意义,但对我而言,更激起了我对母校的怀恋。怀恋而不能重新徜徉于曲园中,呼吸师友的芬芳,对曲园,也就更加魂牵梦萦。这种情感一经母校师友烙印,便刻骨铭心,须臾难忘也。 曲园二张,即其人也。 一张,乃教授古典文学的张元勋先生。张先生乃中文系四大怪之一。说起中文系四大怪,我不甚明了其由来,只是粗略听说四个人恃才傲物,目无纲统,系里开会时四怪就成了主角,会场相逢,一经触碰,便口锋相争,时事世态,古今趣闻,名流雅事,鄙俚街语,学问世理,无一不入辩,加之四人口才好,谈锋健,又当仁不让,俨然会议主角,真正的主持人往往成了旁观者,与会者成听众而甘乐焉。 四怪究竟怎样,我不甚了了。不过张元勋师的博识与健谈在我等入校不久就领教了。 大概是学校地处圣人故里之故,系里在入校不久便组织八九新生游“三孔”,元勋师当导游。时值秋天,曲阜的秋天里似乎总弥漫着灰尘,可能这就是带着风尘味的历史感吧。同样我们这些从各地会于一处的所谓大学生也还没脱尽旅尘,仿佛还散发着火车或汽车的味道,人地生疏,对于一切还很迷茫。那个秋天的下午,阳光不是很亮,秋风还没萧瑟,秋草纷披,路旁的树也初显枯黄之意。我们一百四十多号人,杂乱地挤在孔子故里的某个角落里,纷然不知所往。这时候,元勋师在一旁微笑着看着我们。当然一开始并不知道是张师。是辅导员还是系书记介绍的,我记不清了。我分明记住那淡如秋阳的笑容和那张略显沧桑的圆如朝日的脸。这样的场景在时隔十几年之后越发清晰。有时时间也不会冲淡什么,反而随着它的逝去,一些浮沫和杂滓也会随之被撇去,留下的是真纯的值得怀恋的元勋师那淡如秋阳的笑容和那张略显沧桑的圆如朝日的脸。 还有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健谈的口才。 从来没有想到历史与我们这样贴近,在呼吸之间,在视听之间,到处是历史的遗存,一段残损的城墙,一块风雨剥蚀的古碑,一根古木,甚至一堆乱石,都氤氲着民族源头的烟云:万仞宫墙、金声玉振坊、先师手植桧、大成殿……在别的地方,历史是发黄的纸页上的竖版字,而在这儿,历史是可碰可触的实物。在别的地方,老师讲历史等于纸上谈兵,而我们的张元勋师则用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健谈的口才把我们拉进了具有历史真切氛围的磁场中。 “不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原定一下午游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可是从中午到傍晚,我们竟没逛完孔庙。暮云四合之际,才走到大成殿。也难怪,有这么丰厚的历史积存,有渊博如张元勋师的硕谈,我们有幸躬逢如此盛事,我们甘愿浴历史的长河,我们希望那样的下午能重现,能重温先生的雄深雅健。 “不学《诗》,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在庭训之处,张师言孔子如是说。其时,我等正是叨陪鲤对之童耳。 真的,我们那些学子啊,风华正茂,意兴遄飞,似乎功名事业,立马可待,见绿柳而兴诗,见红棉而怡情,实在是“其新孔嘉,其久如之何”?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不识愁的少年,焉知世道艰难? 时间长了,对元勋师的事也了解渐多。他不但学识渊博,口才好,谈锋健,而且被“钦点”为右派,这实在令人咋舌。 我现在想,他的知识来源于文革前北大的学术圣地和良好的师承,他的健谈来源于他的才华,他的坎坷源于二十多年不便言说的右派生涯。 但历史终究要还原本来面目,张师和他的同辈所遭遇的事,党史国史已有定论,在此不必赘述。然两首诗可见惨痛之猩红: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 诗取自张师的文章《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梦回冷泪”“再觅剪烛”,虽椎心泣血,亦无过之。某次上课,张师谈到一篇文章,是说李九莲如何冤死的,其疾言厉色,与平常之侃谈笑谑的老者大异,能让我等可以想见先生内心深处的哀痛之深。又一日,张师言及曲园一女生坠楼身亡,其言若霜雪,声如铁石,哀恸之情,异于常人。盖当年林昭灼灼其芳,志行高洁,其无端遭祸,张师痛入心髓,大受刺激,故有此激越之举。其中可见张师哀恸之深切。 张师身心担负如此之哀恸,蒙冤二十年,然志节不改,旷达如许。他曾言及自己,在松花江边劳改,看一江春水滚滚东流,其时朝阳东升,云气霭然,先生两手扶腰,目送流水如归鸿远去,宠辱偕忘。其言语不能实录,但上课之情形与先生言及之文人风范竟是历历在目。 最难忘的是先生说到忘情处,竟然蹲到讲桌下作朝日初升状,在中文学子的瞩目之下,一轮苍颜从课桌之际冉冉升起。华发如雪,圆脸如日,冉冉升起者,先生师道之心耳。此瞬间一经定格,是永生难忘的。 先生之举实乃不言之教。他于苍颜华发的“冉冉”中让我们这些即将为人师的师范生让我这个如今仍在为人师的人明白一个老师最根本的师心――亲切平易,如坐春风,如沐朝日。 长者之风,师者风范,而今我在上课之时也有类如元勋师的举动,也幻想能让学生感受到什么,但只不过是换来大多数人的看客之心罢了。偶有几个激赏的学生,我也不敢说已承继张师的衣钵,而只能说亲其风范,爱及他人罢了。 一晃十年过去,我沧桑为师而张师已然退隐,然其《九歌十辩》等丰灵华赡的大作竟如长河激流,喷涌而出,其“石言于晋”“六鹢退飞”等奇谈妙论犹在耳畔,所以虽然困居海隅与张师远隔千里,然心系念之,则虽千里之遥十年之逝,亦如亲承謦欬、耳提面命矣。 也就是在元勋师给我们讲文学授先秦文学史期间,我认识了另一张――张秉禾先生。其实跟张秉禾先生的认识纯属偶然。在写作课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老头来旁听课,或者在别的系别的课上也能看到其人。一开始我们很奇怪,在我们那时还很青涩的青年男女中出现这么一个满脸沧桑头发半秃的老者还是很显眼的,也明显地不协调,故私下呼之“张老头”。当然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也姓张,后来他来的次数多了,从他的自嘲或别的老师的言语间我们知道他和元勋师同姓。我们自以为是中文系的,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如椽大笔,恃才傲物。因此当那老头拿出他写的稿子请我们这些才子帮忙修改,应者寥寥。我记得他一开始与宿舍老四挺熟,可能是老四的兖州口音与曲阜口音相近使然。我和宿舍老四同桌,老四往往把张师之不情之请推脱与我,一来二去我与张老头也就成了师生不算师生忘年交不算忘年交的师生兼忘年交。 他拿他的作文给我看,教写作的修龙恩老师在上面写有评语,其中有“文采闪烁”之句。说实在的,“文采闪烁”的含义我现今也不明白,但秉禾老头很感兴趣,很诚恳地询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文章写得好,很有文采,老师在夸你。张老头一听,竟孩子似的笑了:“我写得很不错吧,文采闪烁!”脸上流露出梦似的幽远的神情,在曲园初夏的午后无尽的陶醉。 可能在他心目中,能解“文采闪烁”的人水平很高,因此时不时地找我给他改作文,有时在教室里,有时在他家里。我和张老头的交往多了起来,与本文相关的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 他早年参加革命,当过新四军。这可在课堂上得到印证。有一次,逻辑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我们在底下作为难状,老师站在讲台上也作为难状,彼此心照不宣。我们是想偷点懒,躲过这一劫,老师也明白这些所谓的才子加学子们的心理,但又不能明言取消,师生便相视而笑。按常例,这样一笑,便意味着我们可以各行其事。这也算时下所流行的潜规则吧。我们都知道,张老头却不明就里,看到我们作为难状,以为我们真的不会,便站起身,慷慨地做一番演讲,大意是他这样大年纪,尚且有信心学好,何况我们年轻,当中又不乏我这样能解“文采闪烁”的高人。说着张老头竟挥起手,唱起了歌,声音苍老而模糊,细听进去,能听出诸如“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词句。以此可见他确实当过新四军,而且他唱时四顾空阔的投入,俨然重回当年铁血岁月。看来军歌中昂扬激奋的旋律激励着他,他也把学场当成了战场。这与当时中文系的课堂和学子的心态是很不协调的。 我们都笑了,说他受了刺激,非有大经历的人不能如此。还真是这样。解放后他进了大学深造,后来又留学苏联,后来成了右派,女朋友也与他分手了。他的经历与元勋师差不多,可能当时的知识分尽子都要经历这一劫吧。无论怎样,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其中的经历非一个沧桑所能说尽也。 几经辗转,他来到曲师,年近半百,娶曲阜当地的一位女子为妻。从日常生活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年龄差异,文化差异,性格差异,收入差异,这诸多差异竟促合这段奇特的姻缘,丈夫搞学术,妻子做清洁工,俩人相伴相守,守护着时光深处最琐碎的生活细节。这在当时的我看来非同寻常,非有大经历大包容的人不能如此。 这样的生活若换成别人,怨天尤人者有之,悲观消极者有之,但张老头却选择了别一样的人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我不甚明了,只是零星地听别的老师说他是我校的第一个复教授,至于复教授为何种名头我至今也不明白。还有一次他拿一封信给我看,信是国外寄来的,上面全是英文,我看不懂。张老头耐心给我解释是外国某权威机构邀请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我不禁肃然起敬,看来他的学术水平非同一般。但是他后来去没去或是什么原因去没去我就不知道了。我从九三年至今,一直在中学教书,教务烦苛,世事茫茫,无从知晓他的具体的事情,身为弱势群体之一员,对于一切事徒有羡鱼之情,能振臂一呼以成全心志,实乃梦想了。 张老头却不这样,他有着自己别样的追求。他把自己的住处命名为“西南园”,屋里挂上“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字,屋外种着几竿修竹或几棵翠绿的花生或长蔓的地瓜。看来他也可能有冥然兀坐,偃仰啸歌的雅兴。还有一张相片,图示某年他种的瓜收获了,他竟专门抱着瓜在萃华园的樱花树下“立此存照”,那得意的神情,使他饱经沧桑的脸上竟平添了几分孩子似的憨痴。 说到孩子,他也提到家乡。他是江苏人,苏中苏北我记不清了,只是依稀记得他老村名中有个“圩”字,当地以“圩”字命名的村很多,他的命运和当地许多人一样,被打上了汊港芦蒲的原生的烙印。他又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家乡已成远方的云树或是日暮天涯的遥想,他最终在鲁西南的平原上,在一座与孔子有关的古城边安身立命。 其时别的同学或忙着准备考研、双学位,或在图书馆里深造,我却在和张老头这样的质朴的人在一起改作文,看西南园的几竿修竹或几棵翠绿的花生或长蔓的地瓜,欣赏着张老头与众不同的怪。 其实不止是张老头怪,在曲园中还有很多可以称怪人的。比如教外国文学的仝老教授,在饭后闲行的甬路上或在课间闲聊的走廊上遇见他,我们可以不鞠躬或呼以“老师好”,而加食指朝他一指,这一指老先生竟也会哈哈大笑,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反而其乐融融。指毕,言笑而过,路遇之礼可算是完成。时隔十几年之下再想这一特殊的礼节,真是百感交集。我现在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每天都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学生关问好,也可为教育之乐吧。但我以为如今的学生的礼貌明显带着程式化的倾向。倒是有几个顽劣小子,见面之后必围而攻之,我避之不及,只有挨几下屁股。在其他老师和同学的诧异目光中,我们的路遇之礼也就此完成。此时我的心际会出现当年在曲园中和先生们的那种其乐融融的一指与一笑。 教育家梅贻琦教授曾提出:“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彼时曲园,楼不甚高,尚有平房如西联一、西联二者,门前大树葱茏,自春及秋,荫庇一方学子之乐土。砖甬泥地,清雨微霜,土气沛然,自地面直入学子心间。园名萃华,曲水亭榭,行者有通幽之叹,也可以留连其间,学圣人曲肱而卧,视富贵如浮云。时节所至,绿树幽竹,各色野花,随时开放。有吐纳古今的图书馆,嗜古者有线装的古书,伴其清茶一杯;喜今者可以马列毛邓,各寻其圣。学不甚严,可以在教室集体听课,可以在自修室研读,也可以黑甜一梦,不知所之。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青野之上,绿水之畔,禾稼声影,惠风扑面,有教授学子漫步其间,可以想学问,也可散逸胸怀。于今想来,那真是曲园最好的光景。而今听说曲园楼高了,地大了,人阔了,我或因杂务忙,或因心绪懒,不能回母校,睹其今日容颜,只能听任曲园的兰花春雨,青石紫藤长存记忆中耳。 我的校友王开岭在《激动的舌头》中这样说:“它(曲师)自有令我怀念和尊敬的地方:学风健正、敦厚;一座藏量逾150万册的旧图书馆;伙食价廉物美;整座校址被庄稼结实地包围,夜晚空气爽魂,飘弋着野菜的懵懂与沁凉,最适于散步遐想——你会为随时打破自然与文明的界线而心情舒畅。”他是以近乎哲人的眼光看待曲园的,说出了曲园赋予学子们的共同感受。 尤其感怀的是,曲园不但是我们的母校,更容纳了像二张这样怪倔至极曾经一度为时代所弃的人,给像他们一样经历坎坷的大师能有最后一方相对安宁的空间来经营他们的学术天地,让他们的芳香的思想随时间而氤氲久远。 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仁慈的呵护,这样宽裕的支持,二张的命运,连同他们整整一代欣逢共和国成立,意气风发报效国家,又遭逢政治运动乃至文革大劫的热血青年,其结局如何,是难以想像的。 雨打浮萍,魂逐野云,天高地迥,号呼靡及。身负古典文人气质的灵魂蒙难一时,竟然在曲园中得以兴寄。曲园给了他们一间办公室,让他们有了一个可以放一本书、一杯茶的地方,有了一个家一个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天真活泼的孩子,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可以延续人类古老的梦想。 更有甚者,曲园因为自己的慷慨仁慈宽厚质朴,成就了两位姓张的学师。 如果说曲园二张的题目有什么兴寓之意的话,可能就在此吧。 说“可能”是心有遗憾的。两位张师之身世际遇表明,古典的文人气质与现代人格的乖谬,似乎是这个深受人民拥戴的政府曾经忽视而又不容忽视的问题。尘世之中可以称为读书人的,如何在时下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中葆有自己的精神、节操与风骨?像两位张师能得曲园荫庇,而所有身负古典情结的读书人,有没有都能有幸得时代或制度的宽容呢? 现代语境似乎不容许传统气质有片言只语,世上诸多的白眼冷嘲可以验证这一点。 写到这地方,笔者也是徒唤奈何。 毕业十几年来,目睹了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感慨颇多。感慨林立的大楼间自然荒野的萎缩消失,感慨在硬性的制度之外心灵的僵硬。我曾向往校园中一方原有的荒原能被保存下来,我曾向往几棵原生的大树能被保留下来。这样一个原生态实际上是让心灵能自由其间,随树而树,随花而花,与高楼相比,也可以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然此自然之心只是临渊羡鱼耳。荒野被迫消失,大树被逼挪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人造的规范与齐整。我曾羡慕远方的那一湾野水黄芦能在这个城市里上演“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古典诗意,我也曾羡慕那一湾河流能自行逶迤,以河流的名义与大海携手,但是机器轰鸣着开进去,原有的水族之类只能在水泥地下前世化石的遗梦了。 由自然之殇联想到学问建树、学人品格与艺术精神的缺失,由曲园二张的特立联想到教育现状中学者理想与偏颇单调的评价标准的碰撞,总觉得身若游离,尘世如梦。 也许是梦想多了,遗世独立,自己竟然背上了怪僻的名声。世俗的话语霸权似乎能主宰一切。自然之心,良善之举,难道真的不适合这个急功近利的世界吗? 写及此,看窗外秋菊正开,秋阳正好,如此也可无语。 但愿这无语能像我对于二位姓张的老师的思念,成熟饱满地垂向自己感恩的大地。 又:此文尚在写作之中,同窗学弟从青岛济南来威海,与之一起在一家川菜馆小酌。言语之间,谈到张元勋师十年来的情况,尤其谈到张师在其间大骂那些在他因病住院期间没前去看望他的那些学生。那些在张师患病期间没能前去探望的人中,当然有我了。我这个不能挣脱环境束缚的行动的侏儒只能咽泪装欢,在友人的诧异中却道川菜麻辣了。 而今心痛犹隐隐,然更敬其刚正,他不是那种虚浮的人,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怪异之处吧。骂得狠,骂得绝,这骂如当头棒喝,教人知道这世上还有豁朗如许。 想到毕业离校时与元勋师话别的时刻,想到临别时张师的嘱托,唾面自干,也只能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