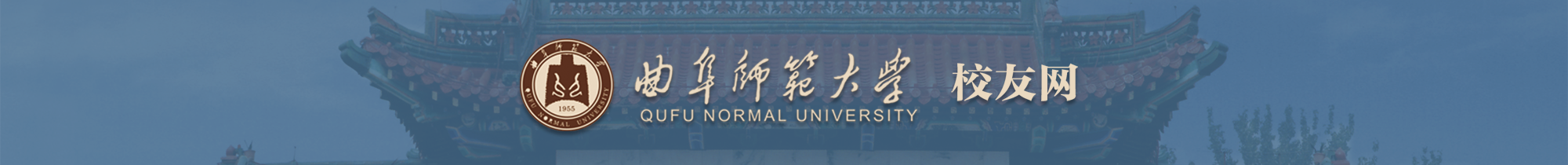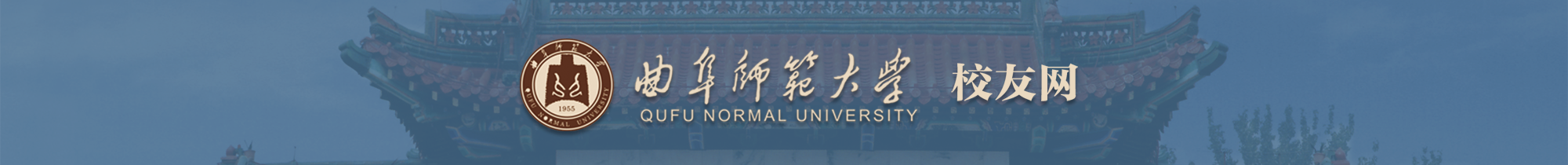退休后,过起了悠闲淡泊的生活,犹如秋天的原野,坦荡而清净,实在是一种人生凝重而天然的享受。 教师节来临之际,任淄博市教育局局长的学生张洪亮,敲开了我的门,笑嘻嘻地说:“老师,节日好。”随手捧上了一束绚丽的鲜花,令我一时感动不已。 送走洪亮他们,思绪宛如一湖秋水被风吹过,激起了一道道涟漪,令人追溯自己的脚印,忆起如星恩师…… 一 1959年暑假开学后,大概是因为我在初中时曾当过淄博三中少先队大队长的缘故吧,被淄博一中团委书记许锡川老师选中,提名为校团委委员候选人,且被选中,令我感到既诧异又兴奋。一下子融入了一个团结和谐的领导群体之中,由此激励我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当时许老师与我们不分彼此,几乎像同学一样,无话不谈,无事可瞒。许老师在索镇学习时,我与我们班团支部书记黄宗志骑自行车去看他,他格外高兴,盛情招待我们。我们临走又给准备好了路上吃的,送我们时泪眼汪汪,伫立村头,直到看不到我们的身影。有一年寒假,他竟然从潍坊到博山的途中下火车,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20多里来到我的家中,看望我的母亲与我,感动得母亲久久地拉着老师的手,说不出话来。 1960年春,由许锡川老师和张陶村校长当介绍人,一中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这对于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来讲,该是何等的喜事啊!可是,当时市委组织部一位组织员与我谈话时,说我有骄傲自满情绪,后来就以此为由没有批准。许老师约我到他家吃了一顿白馒头,然后才告诉我这一消息,他说:“组织上入党是一个手续,而思想上、行动上入党,则是终生的实践。福信啊,要经得住组织的考验,经受住一切挫折。”在许老师的教诲下,我逐步认识到,此事对我来讲无疑是件好事,给我提供了一次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机会,经受了一次锻炼。这样的教诲,使我终生不忘,由此我铭记只有永远不自满,才能不断进取,不断进步。 1989年10月24日,我率张店区有关部门领导去胶东考察,返回途中有意路经坊子区许锡川老师的老家,看望久别的老师。坊子区委书记孟庆臣,是我在省委党校县委书记学习班的同学。我一到他那儿,就请他着人去请许老师。当许老师弯着腰,步履蹒跚地进入会客厅时,我看到他脸上布满了皱纹,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不禁一丝惆怅掠过我的心头,但他依然是灿烂地笑着,使得脸上皱纹更加集中。他与我亲切握手,眼里闪动着泪花。我请他坐下,恭敬地给他捧上一杯热茶,真切地说:“许老师,您是我的恩师,没有您的醍醐灌顶,就没有我的今天。老师的恩情,我终生不忘。” 吃饭时,他紧挨在孟庆臣身边,显得非常激动,以致手有点颤颤巍巍地把酒溅在饭桌上,全然失去了当年的潇洒和干练。但他对生活,对学生,依旧乐观热情,临别久久地握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福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感到非常欣慰。有了这餐饭,得到了你的那么多同事的敬酒,特别是我们父母官的敬酒,就足矣了。”他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可我早已泪眼模糊。 我送许老师上车,在招待所门口与他挥手告别。此时已是深秋季节,北风吹拂,颇有凉意,直到载着许老师的车子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我望着满天星斗,心中隐隐地涌动着莫名的凄凉,久久地伫立在老师家乡的土地上…… 后来,他的孙女来我校上学,带来了他的一封信,字迹俊秀,其情切切。再后来,他的孙女给我带来了许锡川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的心头一惊,悲痛顿生,泪水涌出,扔掉手头的工作,索性走到校园里,仰望长空,寄寓东去的悠悠白云,请她满载我的不尽哀思,告慰我敬爱的老师…… 二 考进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后,我充任班团支部书记。1964年秋,我们即将毕业的学生参加了曲阜县农村“四清”,我被分配到城南葛家庄工作组,组长是我们的党总支书记阎金玉。他18岁任许世友警卫连指导员、23岁当团参谋长、25岁任副团长,在朝鲜战场上由于患肺结核,回国疗病并转业。我们一同睡地铺,食窝头,耕田地,捉虱子,一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书记与学生的沟壑荡平了,官兵一致了,友谊油然而生。 这样的生活常常引起他的追思,不断地引领我们与他一起去翻阅那火与血写成的无字天书,从而锤炼我们那颗追求理想的心灵。他不仅言教于工作生活的细微之中,而且更注重以身作则,垂范于时时刻刻。他的肺大泡致使他经常彻夜咳嗽,难以入眠,白天却依然精力饱满地投入工作。他的夫人是位大夫,经常着人给他捎药,而他入村两个多月一次也不曾回仅隔十几里的家。在那越“左”越革命的年头里,他宁愿被人斥为“右”倾,也不加害农村干部。当有些人侵占了一户老中农的树林时,他坚决主张予以退还。结果与副组长发生冲突,直到团部来人支持老阎,才算了断,才安定了民心。我有一次在小组总结会上,既讲了我们的成绩,又讲了我们的不足和今后的建议,他高兴地说:“小张,开始运用辩证法了。” 那时农村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匮乏是孪生的。新年到了,我们与社员一起联欢。他带头唱起了《白毛女》选段,引起大家不断喝彩。他又掏出工资请社员看了一场电影,开创村里放电影之记录。 1965年4月3日,沐浴着和煦的春风,环绕着新绿的杨柳,聆听着布谷的叫声,在工作组的茅草屋里,金玉书记亲切地说:“小张,我高兴地告诉你,经组织批准,你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从现在开始就要把一切交给党,争取做一个好党员。” 我毕业分配时,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但当时充实基层要求年龄要小一些的,故在省里调整方案时,金玉书记调我到菏泽充实基层。我临走时,他约我到他家吃了一顿红烧肉,并语重心长地说:“福信,到省委办公厅去工作,当然好,但我觉着你相对年龄小一点,更应该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和考验。” 鲁西南在山东相对而言,比较贫困和艰苦。当年全省数十所大学应届毕业的28位同学一起充实到菏泽专区,先作为普通队员参加当地的农村“四清”,我被分配到菏泽县吕陵公社“四清”大队桑家庄工作组。因为有了在曲阜参加农村“四清”的实践,所以在这里工作起来,就比较熟悉,比较容易。我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照上级的要求有步骤地进行“四清”,组织生产。 我的组长是一位公社党委副书记,文化程度不高,但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我与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就与他一起睡地铺,一起在一个贫农家里吃饭,一起在他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工作,锤炼对党的无限忠诚,培育同老百姓的血肉感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富有经验的老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日积月累地增长才干和经验,逐步适应承担的工作。 1966年春天,我的预备党员刚刚被批准转正,菏泽县“四清”工作团委派我到赵楼“四清”分队任指导员,后任赵楼公社党委书记,成为我们大学生队伍中第一个分配具体工作岗位的。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经过一番折腾,我们这些充实基层的大学生被污为刘少奇、安子文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产物,必须予以纠正,我回到了家乡淄博。 1988年春,我任中共张店区委书记时,阎金玉书记突然光临寒舍,我惊讶之际,询问他的近况,他笑哈哈地说:“我与病魔苦斗了近40个春秋,现在看我是胜利者。”他依旧是挺拔的身材,高高的个子,单薄的身躯,炯炯的目光,富有哲理的话语,凝聚着不屈的意志。时隔23年后,再一次与金玉书记相聚,又一次聆听教诲,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在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金玉书记去世的消息,是曲师大党委书记谷汉民告诉我的。那时,金玉书记已魂飘泉台月余了。这迟到的哀思,更深沉更久远,如昨的往事,如涛的哀愫,回荡心中,不能自已,凝聚成一篇《迟到的哀思》发表在曲师大校报上,曾引起许多师生的关注。后来,应母校之邀,回到学校,伫立在美丽幽静的校园里,伴随着如泣如诉的风声,耳闻王化岱老师的话语:“老阎有着钢铁般的毅力,他与肺大泡、肺癌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临终时说:‘在火与血的锤炼下,锻造了党性。使我为党多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十分的欣慰。’”这凿凿之声,扣打着我的心灵,激励着我们这些阎金玉书记的弟子们奋勇前行,去不断地开创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