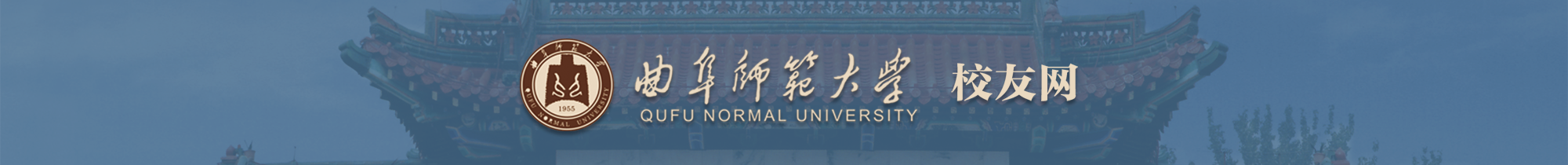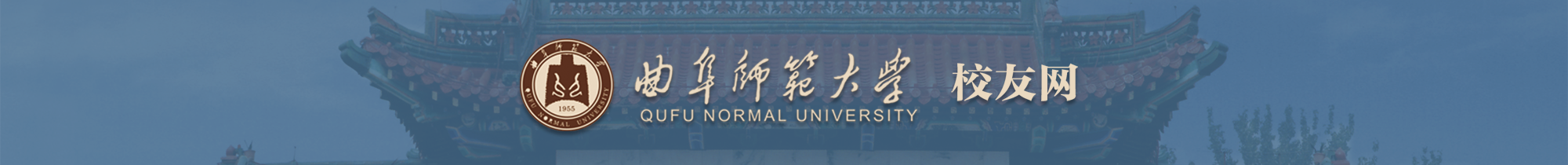张元勋教授和他的弟子们游览曲阜周公庙 2013年4月12日中午,忽接金杰短信,张元勋教授走了。 他走得如此突然,但事后想来早有预兆。早在二十多天前,3月22日,我短信贺他喜得贵孙的时候,他竟回复: 百姓之子生在草芥平民之家,一生拮据,仰人鼻息,我们能给孩子准备何种优裕?无有也!望之襁褓之中,吾甚凄然也! 我因替他高兴,接连用短信给他开了一些玩笑,“硕士之子,名士之孙,尚称草芥,我等寒门,可有出路乎?”“望之凄然云云,喜极而泣也,所谓喜泪纵横,不知所云!” 然而隔了整整一天,他才给我回复,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昨日一日,家中人众辐辏,盖装修工三人、学生五人在焉,工者零修室内原装诸开裂处,学生为帮你师母为我褥疮清洗换药。于此之间正与足下短信往还,故应答失次,最后非其时而毕!今日再翻阅,以不知所云之句最佳!此诸葛之名句也!深沉痛切,情可动人!然刘阿斗无动于衷而蜀汉亡!来者不肖,子孙满堂又如何?故,陈涉曰: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即言此!足下少时生活困顿,我于系偶闻诸末论,心悯而不能申也!足下于四年潦倒历练中,置系内诸小人之鄙夷若兽嚣枭鸣焉,我行我素,乃至今日之成就!孔子曰:“吾少也贱!”此之谓也!关于贫贱,孔子之一生都谆谆于口,未尝辍其论,一部《论语》可挑出三分之一的篇幅论之,夫子不忘己非名门贵胄,但他有曲肱而枕之的自豪情结!足下与我,岂非儒家之忠徒乎! 他此后又问一诗友的父亲现居何职。我回得很快,“应为裸退!” 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恩师与我最后的对话,也是我们师生21年交往的回顾和总结! 天涯何处无知音 次日赶回曲阜。人间四月天,正是曲阜师大校园里姹紫嫣红,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方近楼前,便见张师门口斜放着一枝白色的樱花。这一枝小小的白花,花瓣低垂,几近枯萎,和旁边堆放的花圈相比,大相径庭,但毫不逊色。师母后来忍泪说,这是中文系一位不认识的女生,闻讯后从校园里的树上折下送来的。她曾经相约,等张老师好了,推他去看满园的鲜花。 一生愤世嫉俗却又满腔热情、挚爱学生的张师再也看不到这些鲜花。遗像中的他,依旧白发戟立,目光灼灼,似乎一开口,又会发出慷慨羽声。遗像两边挂着我清晨拟写的挽联: 就道红楼,长诗惊风雨,千磨万折,何尝零落英雄胆; 弘道杏坛,壮文传天地,九歌十辨,不曾拘束名士魂。 “就道”和“弘道”,语出《论语》,后来成为曲师大著名的一个典故:约1995年,学校新图书馆落成,大门处有一牌坊,须两面题字。应题何字,一帮领导和教授争论得不可开交。所提的“方案”是:牌坊正面刻“改革开放”,背面刻“创新求实”,还有主张刻“书城”“书海”等等。张师一开口,便语惊四座,建议进门题“就道”,出门题“弘道”。至今这几个字,还铭刻在那里。他少年负笈北大,为《红楼》编委,因与人合著长诗《是时候了》,搅起惊天风雨,惹下弥天大祸,身陷囹圄8年,驱逐流放14年,然“虽为叛徒所鬻,为鹰犬置于刀俎,遍体鳞伤,一身清白,不曾为犬,不曾卖友”,堪称英雄;后来执教曲师,狂狷豪迈,不媚流俗,开口嬉笑怒骂,行文汪洋恣肆,多有著述,《九歌十辨》嘉惠学林,的是名士。 师母见我在灵前默立,含泪前来,我便强忍哽咽,一字一句给她解释。师母说,“你是最理解他的人,你是最了解他的人!” 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不知名的女孩折来的那枝小小的白花。它曾经是有生命的,是那么的真实,不带一点虚伪和应付,胜过所有的花圈和挽联。我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张师也未必知道,她也未必受过张师的教诲。但她又何尝不是张师的知音!天涯又何处没有张师的知音! 不曾拘束名士魂 我读书的时候,曲阜师范大学还是一所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农村大学。学兄金波写得好:“僻处一隅之鲁城,已衰沦为寂凉小邑,鲁王歌舞繁华之地,尽为稗草丘墟。学校处城之西郭,接农舍,近田垄,白首先生,布衣学子,与耕夫渔樵常相杂处,书声琴韵,每与鸡鸣犬吠相通闻。而经书既设,问对既成,陋室荒园中自有一股静穆弘正之气摩荡之,与金声玉振余音相发挥,五十年来,渐次浸染,遂使斯校重焕杏坛设教之风采,而成当今求学问道之佳地。” 就在这里,1992年,我是中文系一个穷困潦倒、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的农家子弟,读大二,张师教我们先秦文学。当时就是校园里的传奇人物。 他的学问实在是太好。1979年,他的“反革命”加“右派”罪名平反以后,“就地安置”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据中文系79级、80级校友回忆,学校面试时,让他在毫无准备且无课本的情况下,讲授屈原的《离骚》。而他在远离校园、囿于牢狱和农场二十几年之后,脱口背诵《离骚》原文和注解,并淋漓尽致加以发挥。 他的见闻实在又太广。据校友回忆,某年带领学生游三孔,大凡相关的典章制度、诗词文赋、世情民俗、谣谚俚语、故事传说,张师无不信手拈来。讲至星宿运转轨道与留痕,竟随手抄起路边的一把大扫帚,旋舞得呼呼生风。最后,学生们成了听众的一小部分——几乎所有的游客都被引了过来,导游都听得呆了。人越聚越多,竟至浩浩荡荡,就这样一路徒步行至孔林。大半天,无一人掉队,无一人叫累,见者无不称奇。 我至今记得他上课何等与众不同:阔步登台,不携片纸,睥睨天下,口若悬河。他懂的如此之多,但家中的藏书却又如此之少,当代小说没有,五四之后只有鲁迅全集。他见识又高,经历又广,每每口讲指画,纵论古今,指陈时事,臧否人物。记得他曾调侃一位同学的“诗”,是“抽棍打腚啪之流也”,他接着介绍何为“抽棍打腚啪”:一位老秀才写诗记述夜行骑驴遇狼:“出门遇二马(马虎,山东话是狼),抽棍打腚啪,幸遇邻人甲,把呱二更啦”;他讽刺没有文化的人装有文化,“我会作诗信不信,好歹也是知识分子”;他解释《诗经》“以尔车来,载我贿迁”,就是男生骑着自行车,把女生从五号楼拉到七号楼去;他讲《左传》“六鹢退飞过宋都”,忽停笔发问“何故”,谁也不知道何故,他于是做大鸟退飞状,厉声说,“风疾也!”他描摹曲阜西关的小痞子劫财得手,“呼啸奔腾而去”,诸如此类。我当时年少轻狂,从小到大,没记过一个字的课堂笔记,唯独上张师的课,总是记得手腕疼,笑得肚子疼。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因一篇文章获他赏识。他大概知道家父因“文革”磨难,早年去世,狐伤其类,对我有些另眼相看。承他不弃,日益熟悉,渐渐把他家的客厅当作了第二课堂,他家的厨房当作了第二餐厅。 他极好客,每逢过节,必要我招呼四五同学去家吃饭,大概是深知我们腹内空空,总是把酱牛肉、糖醋里脊之类,铺陈满桌,任凭我们狼吞虎咽。他也偶尔指使我们干一些小活儿,记得一次是为他家的小院扎编篱笆,结果编得东倒西歪,他并不气恼,批评一句“胡编乱造”了事。他极富诗人气质,常说,左手持蟹螯,右手持《离骚》,饮美酒,读美文,方为真名士。一有空,便带领我们踏青郊游,遍寻古迹,临风舞雩台,濯足南沙河,月夜说聊斋,陋巷吃馄饨,无所不至。 如果是三流老师教知识,二流老师教方法,一流老师教思想,毫无疑问,张师就是典型的一流老师。1995年夏,张师六十岁生日到来之际,行将退休。而他的最后一课也是与众不同。 那天下午,除了我和洪涛之外,任何人不知道他即将告别讲台。他给前来上课的同学,每人签名赠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九歌十辨》,书的扉页上特意盖了一方印,他将印文写在黑板上,“凭此记,乃是我弟子!”我们则给他送了一件写有“好人一生平安”的T恤衫,并签上所有人的名字,他视若珍宝! 当晚,我与洪涛一行人等,在当时的蓝房子请张师小酌,也算为他祝寿。据说,张师是不喜欢过生日的,也不准学生给他过生日。原来,在生日这天,早晨起床之后,他总是赤身裸体,朝着埋葬母亲的方向——他的故乡,给母亲磕头……因为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在监狱里,未能为母亲送终。 这是我们第一次给他过生日,他并没有说些伤感的话。虽退休,但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常言“生活从六十岁刚刚开始”,颇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之感。是晚酒至半酣,举座皆欢,不免饮诗作对,误者,我以掌击其背,张师含笑詈之,称:“行若李逵,状若厉鬼!” 这样不知不觉,我们也该毕业了。1995年7月,我与同窗金杰,去和张师告别。张师兀坐沙发,有些不苟言笑。他取出我昨天拿来的毕业纪念册,仅一个晚上的时间,他竟用铁画银钩之笔,整整给我写了十七首绝句!前面两页写不完,他又标明下转第多少页,依稀记得有: 前岁君归来,赠我黄黏米。黏米厚如斯,不可析肌理! 去岁君归来,赠我商羊胕!江河有大水,酒香瓶初透! 临行,我说,张老师,我走了,给您鞠个躬吧!他依然兀坐不动,如同那年他带我前去拜望的林庚,“像一截枯木头”!我鞠了三个躬,眼泪夺眶而出,夺门而去,上了金杰的自行车,一直没有回头。直到拐弯,看到张师一直站在那里。 他在我的毕业纪念册里写道,“1992年,对我而言有两件大事,一是我的《九歌十辨》得以出版,二是我的院子里闯入了一个叫李岩峰的青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最最好的好朋友”! 后来,我在与他的短信中说: 师幼承庭训,弱赴京师,长历风波,壮隐阙里,息影杏坛之侧,驰骋三孔之间,假瓦釜以为钟,雕朽木以为器,诗人之性、士人之风一身兼之,才情识三者俱备,何其难得!思百载以下,曲园明月不知将照何人!天地造化尚能生你我师徒声气相投者乎! 张师晚年对此信颇为看重,特于去年,嘱我命善书之同窗瑶琴,“书成条幅,悬之目侧,是为至嘱,切切!” 百折不挠英雄胆 对于张师的胆识和风骨,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母校老师之中,与余影响最深、交谊最好者,为张元勋老师。余尝言,曲园倘无张师,当打折扣,少风骨,减光彩。北大百年校庆,余从张师前往观礼。燕园名儒大师者不知凡几,学子扬名立万赫赫有成者亦不知凡几。然张师以一肄业之本科生,凭余亲眼所见,上自林庚、陈贻焮,下至谢冕,无不对之待若上宾,礼敬有加,细诘之,非为学问,人品故也。 张师当年以超迈绝伦之才,编《红楼》,创《广场》,新诗《是时候了》如洪钟大吕,在新文学中立不灭之地,终被飞来横祸,陷不测之险,忍非人之辱。当是时也,同学中背师者有之,卖友者有之,作伥者有之,吮血者有之,然张师自始敢作敢当,未尝推一事、害一人,在众人避之不及之时,以戴罪之身,未婚夫之名,毅然独自前往,南下探望林昭,留下一段井台会、蓝台会的佳话。去年,又以衰病之躯,霜雪之姿,撰新著一本,行文汪洋恣肆,遍布珠玑,名播海外。直至今日,仍笔耕不辍。噫!有此恩师,真不负曲园四年也! 判断一个人的成色,不仅要看他的朋友,也要看他“对手”。张师昔日的同窗、后来的“论敌”,《是时候了》的共同作者沈泽宜曾经说,“张元勋最伟大的事是后来到狱中探望林昭!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辉煌!”世人皆知张师南下探望林昭,世人皆不知张师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从1968年7月7日起,他被单独关押于一处被五重大门封闭的曾储存剧毒化学品的仓库之中,长达138天,每天都有被处决的危险。事情的起因,是1968年4月,张师又以回青岛探家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林昭未果而超假,并由此被追查出1966年的第一次探监,而对其进行重新审讯并被关押。这便是被他后来称为“鳄鱼之胃”的地方。 张师为何要做如此冒险之举?正如他一同学所说: 他千里迢迢去探视狱中的林昭,不是为了爱情,也不是亲情,说是为了友谊还不足以概括这件事的原因、结果和价值。其实是为了被中国人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义”字。张元勋也把这个“义”字张扬到极其高不可攀的高度。在那个时代,朋友之间反目成仇,亲兄弟形同陌路,夫妻相互揭发,……为了生存,人们抛弃了“义”,实在是无可厚非。正因为可以原谅某些“不义”的弱者,而更不应该忽视“大义”的强者。像张元勋这样,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不计成破利钝,丝毫没有私利的考虑,做好了一切最坏的打算,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他也确确实实承受了第二波打击,这绝不是一般芸芸众生能做出的事情。是仗义豪侠,是义薄云天,是替天行道,是可以和程婴、公孙杵臼相比的义举! 经历了这样的折磨,使张师很容易看淡生死,但他始终认为不会死。2002年张师被查出食道癌,已是后期,先是手术,将食道下端贲门与胃的一部分割了十厘米。当时,我去齐鲁医院看他,他犹在病床之上侃侃而谈。张师大哥张翰勋,山师大古典文学教授,知我来济,一定要见我一面,询问北京有无良医,我慨然允诺。翰勋师含泪告,张师手术前夜,生死未卜,还致电与他,询问“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上句,他思绪混乱,应对无方。次日晨八点,电话忽响,他惊疑不定接听,竟是张师在护士推进手术室的途中来电,说,“我记得了!是‘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术后,连医生都宣布回天乏术,劝其回家等死。张师自己写到,“有客自草原来,诊脉良久,曰,天不罚善!”从此,他又开始喝草药。药量之大,我所亲见,有数麻袋之巨!侥天之幸,自从喝了这奇苦无比、奇多无比的草药之后,张师原先转移肿大的淋巴结竟然渐渐消失,医生宣布:居然痊愈了!这是后话。 此去莫叹知音少 2003年7月,我们又回校给张师祝贺七十大寿。我们感觉,张师怕是难过此关了。两年后,2005年7月,返校赴毕业10周年之约,又拜见张师。我有一文记其经过: 张师又经大劫,发白如雪,正金波学兄所谓“花开花落,庭树茁而屋宇旧;人去人回,后学秀而师慈老”,所幸精神健旺,声音洪迈,思维敏捷不减当年,高声诵读陶渊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之句,酸人胸臆。 次日,男生三四人,女生四五人,与张师一起重游舞雩台。千年古台,无非黄土一抔,当年黍禾离离,张师飞车而往,健身而上,今策杖徐行矣。又至周公庙,庙内芳草萋萋,寂寥依旧,远客忽至,宿鸟惊飞,师徒应对,顿增生气。张师博闻强记,问一答十,虽碑文漫灭,如数家珍,逐字讲解,于唐槐汉柏之下,红墙古院之中,传先贤之遗训,发玉振之金声。噫!师慈已老而后学未秀,明日归去,案牍复积如山,应差奔走如电,虽欲优游林下,长聆师训,岂可得乎!此地一别,尚不知后会何期。乃为诗曰: 苍苔侵阶径未扫,宿燕低飞惊客早。 古树曾经旧雨露,断碑方生新蔓草。 恍见恩师白发多,不觉故人红颜老。 十年风雨一杯酒,此去莫叹知音少。 张师很满意我的这篇《游周公庙诗并序》。乃命我的同窗、素有军旅书家之称的沈瑶琴,书以巨幅,精工装裱,悬挂于客厅最醒目处。此后凡有访客合影,必以此为背景。 2012年7月21日,我们再次齐聚曲阜,为张师祝贺八十寿辰。此时的张师,连策杖也不能了。他因一次摔倒,导致全身几近瘫痪,又动了两次大手术。我们将他从汽车里扶下,五六个男生抬着轮椅,一直将他抬到二楼宴会大厅。 金杰等人已经将会场布置好,正中悬挂祝贺张元勋先生八十寿辰横幅,横幅下悬挂刘守安老师亲笔书写的寿字,寿字下数行小字,引《论语》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为仁者寿。弟子们送了一份十几米长的孔子圣迹图作为贺礼,大家手扶长卷,围绕张老师坐椅徐徐展开,依次移动,张师致辞,几度哽咽。此后我们开怀畅饮。然而谁也不曾想到,此时,北京正在经历一次61年未遇的暴雨,我们正在经历和张师的最后一次欢聚! 驾鹤回望应有笑 2013年4月14日。告别现场,我们含泪送张师最后一程。工人们把我写的挽联用电脑喷绘,从殡仪馆的二楼垂落下来。送行的人们一眼就看出来,这帮人真是太马虎了,他们居然一边打错了一个字,“就道”红楼,打成了“就到”红楼,“壮”文打成了“状”文。一个两眼哭得通红的女生跑过来问我,是不是换下来。我说不用,张师一生,从来就不拘小节,从来就充满了太多的缺憾。他一生调侃别人没有文化,最后却被没有文化的人调侃了一把。他驾鹤西行,回首俯瞰,一定会笑出声来的。 这时候,身后的綦维突然说,“张老师如果有知,他一定不会哭。”“知道吗?张老师是三月三那天走的”。我不解。“上祀节呀!”我依然不解。雪艳说,“奔者不禁!” 我们都含着眼泪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