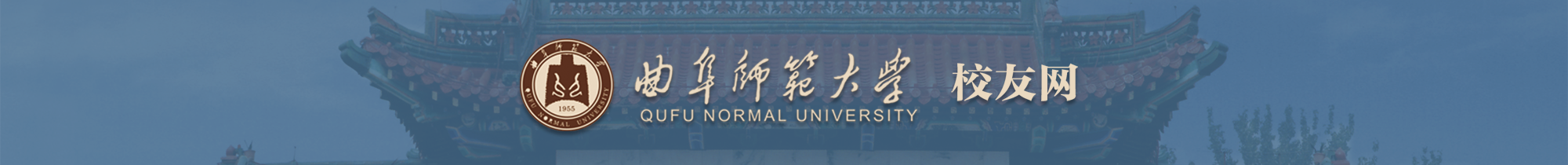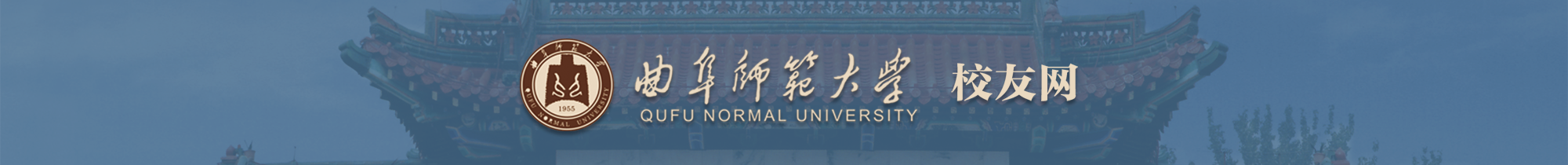韩军先生简介 韩军,男,1962年生。1986年毕业于我校中文系,获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全国著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育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获得者、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一等奖获得者。第一线中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教师之友》杂志核心作者。现任清华大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主持全国最大语文教育论坛“韩军在线”。 1993年1月,在全国语文教育界首次提出“人文精神”的概念(比文学界早半年),由此引发90年代持续多年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语文教育大讨论。2000年9月,发表《“新语文教育”论纲》,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新语文教育”概念。代表著述,《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语文学习》1993年1期)、《反对伪圣化》(《中国青年报》1999年6月7日“冰点”专栏)、《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2000年3期《中学语文》)、《文就是道--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之思》(《山东教育》〈中学版〉2000年1、2、3月连载)、《“新语文教育”论纲》(《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17期)、《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问题与对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三环节强化教学》(《师范教育》1996年2期)等。 一、想弃读:父亲让我蹲禁闭 24年前,夏天,一个傍晚。 我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是山东省德州师专中文系的。那年,我17岁。拿到通知书,万分失望。我是当年那所中学考上大学的唯一的文科生。我的同学,最差的也去了二类学院,是本科,而唯独我考上了一个专科,并且是师范院校。我坚决不去,准备复读,第二年再考。 但是,爸爸却坚决让我读师专,不同意我复读再考。爸爸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干部、老党员。他解放前参加革命,在大熔炉里中识得几个“字儿”。他识字水平,是能粗浅阅读山东省的党报《大众日报》,但却不能写作。他写的“字儿”,我更不敢恭维。 也许是出于他自身对文化的渴望,也许是出于对儿子未来工作的忧虑,他执意让我读师专。如果我去上学,将是我们韩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位“先生”。而17岁的我,出于青春豪情,出于对自我“宏大前程”的神往,执拗不去读师专。 爸愤怒了:“上师专怎么了,当老师很不错,知书识礼,自己识‘字儿’有文化,也教别人识‘字儿’有文化,你又能挣碗饭吃,很不错嘛!” 我说:“我要考法学院,当律师;我要考广播学院,当播音员(当时还没有主持人概念),将来社会发展,更需要两种人才”。 爸爸说不过我,就对我施行“专政”。把我锁在一间小东屋里,不许出门,不许吃饭,让我反省。我呆了一整天。不时有邻居和朋友,隔着门缝、窗户劝我:“听你爸爸的话吧,他是老干部,说的有道理。” 我硬着头皮,带了行囊去师专。 父母一同把我送到学校。母亲为我铺好床铺,并把手表摘下来,戴在我的手上。那是我们家的高级家当,瑞士产的,母亲戴了没几年。 然而,两年后,我即将毕业当“先生”前夕,爸爸却被诊断出肺癌,我走上讲台不到三个月,就离开了我,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手执教鞭的“英姿”。 那之后十几年,一本教育杂志的头条,登了一篇长篇报道,那是我的“光荣事迹”,上面还有我的大幅照片。从此,我成了所谓“名师”。爸爸已经永远不可能看到儿子那“踌躇满志”的样子了。 我把那本杂志当成了“纸钱”,奉献在爸的坟前。没识几个“字儿”的老爸,若地下有知,说不定,能读到上面那一长串“字儿”,――那是关于他儿子的,能看到已成壮年的儿子的照片,——他儿子“有出息”了。 我不曾忘记,老革命、老党员的爸爸,在我走上人生的,“侵犯”我的“人权”,“强迫”我读师专,正是我为师的起点。某种意义上,是老革命的爸爸让我手执教鞭的。 今日,我坐在电脑前,回首22年前,那被“关禁闭”的情景,泪水滴湿了我的键盘。 二、欲转行:做教师难说最爱 1981年,我19岁,从德州师专毕业,我的选择,不是做老师,而是做电台播音员。 那时,正是一个著名故事流传的时代。那故事说的是,一个公社书记对一名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售货员!这个故事并非虚构。连售货员都比教师待遇高,播音员肯定比教师高多了。那时,电视机远远没有普及,广播拥有大量听众。播音员、记者走到哪儿,一说,“我是电台的,就是那个播送什么什么的播音员”,肯定把人家“惊吓”一下,立即引来仰视艳羡的目光,把你前前后后打量一番。 即使今天,你也得承认,一个中等学校的老师,其社会地位,仍不一定比得上市级电台的一个播音员! 我在师专里一直做播音员,由于我的播音及朗诵水平特别出众,被市电台看中。做播音员,对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这种诱惑力,主要产生自青年人的虚荣心:自己的声音被无线电波传出去,让全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侧耳倾听,能不荣耀?再就是播音员待遇高,社会地位高。 当然,最终,电台没有去成。我去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任教。 做教师,本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不是我最爱,执了教鞭,是不情愿的。换言之,并非我选择了这个职业,而是这个职业选择了我。 11年后的1992年,30岁的我,对教师职业仍没有本心的认同。山东省筹建经济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开招聘主持人,此消息使我又一次“蠢蠢欲动”。 经过与全国各地成百上千人的竞争,一点不出自已意料,我又被山东省广播电视厅录取了。我就要进入省城,成为省级电台的记者和主持人了。 省电台百里迢迢来校要人,学校领导不放人,这同样不出人意料。 最终,我还得做教师。像一头笨拙的奶牛,被扭着脖颈,强行“按”在槽上,吃草、下奶。 三、第一课:“后生”给“先生”授课 难忘第一课的情形。1981年,我被分配到德州市临邑师范学校任教,当时我19岁。 我走上讲台的第一堂课,是为别人代课,台下是一群大龄民办教师。来自极偏远极穷困的农村小学,年龄大都在二三岁,有的四十岁。我作为“后生”给“先生”上课。 看到台下那么多陌生而成熟的眼睛,我有些慌张,前半节课,我还能坚持用普通话(即“洋话”)讲课,后半节课,就镇定不住了,不知不觉改用成了家乡“土话”。如此“土”“洋”承转,就像唱歌“跑调儿”一样,好笑,滑稽。 但,台下有着十几年教龄的民办老师们,强忍住不笑场,耐心听我把课读完,我由衷感激他们。 我哪有什么讲课艺术!但听课的民办老师们,却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把我的话认认真真笔录下来。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震撼,第一次真切触摸到“老师”二字的实在意义。 我只给他们代过几堂课,但,这些大龄“先生”们,在以后两年多的在校时间里,碰到我时,都恭恭敬敬称我为“老师”。还不时拿各种问题、作文来询问我。 二三十岁的“先生”们,却喊19岁的“后生”为老师,我自然窘迫异常,之后,就愈觉得重任在肩,鞭策在心:我这个“老师”能对得起他们吗?我这个“后生小儿”能用他们那种坚忍的求学精神,当好老师吗?学问上,我或许比他们多那么一星半点,而精神上,他们比我峻拔,伟岸,他们才是我永远的“先生”。 那之后几年,我骑着自行车,为全县几个乡镇的民办教师授课。有一次,路遇车祸,路边巨大的水泥电线杆被汽车撞倒,电线杆又顺着我的腰部蹭下来,把我从自行车上扑倒,我昏过去。多亏抢救及时,命没丢,但落下终身的腰疼病。 与其说,是“后生”的我,把新鲜的知识送给那些“民办”“先生”们,不如说,是乡下“民办”的“先生”们,在中国穷乡僻壤、在中国的最基层,默默无闻、埋首从教的坚韧精神,一直感染着我。 如今,我成了所谓“名师”,而他们却是无名者。他们或许早转正了,或许仍然“民办”着。 中国教育的脊梁,无疑是他们。 四、苦与甘:埋头攀登不问高
不认同这个职业,一点也不表明我不敬业,恰恰相反,我同样像一头更踏实的耕牛,不倦劳作,如一架充足了电的机器,不敢休闲。 我任劳任怨地为这个职业而努力,为孩子们付出,踏踏实实卖力苦干,心无旁骛,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耗在学习上和学生身上。 那是一个酷暑,烈日如火,蝉声鼎沸。 全校老师和学生都午休了,我批改完当天的作业,打开收音机,继续收听天津教育广播电台播出的文授课节目。 刚走上教学岗位,深感知识不足,想继续在职深造。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天津电台播出的中文系授课节目,授课的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我如获至宝。于是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收听。 我一边收听,一边借来学校的单录机,扣在自己的收音机上录音。 由于整天备课、上课、批改,再加上熬夜听课,过分疲劳、困乏,天又太热,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醒来时,倒带,重放单录机,核对笔记,居然从里面传出了我的呼噜声。 就这样,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收听广播,坚持了三年,听完了又把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听了一遍。并且,我根据录音,一字不落地记录下了讲课的所有内容,我的记录手稿,摞起来足有半尺厚。如此,我等于又上了一个大学。 第一,由于我的埋头苦干,我赢得了全校老师的肯定。我连续多次被全校教师投票,推选为市级、省级优秀教师。优秀教师名额极其有限,每次只有一名。而我成了全校获得荣誉称号最多、荣誉级别最高的人。而每次,我的选票都遥遥领先。 第二,1991年,我参加全省教学能手抽签讲课大赛,与全省选拔出来的几十名“精英”教师同时竞技,最终,我被评为全省文科组讲课第一名,荣获“山东省教学能手”称号。同年,还被推选为“山东省优秀教师”。之后,我又被评为“山东省骨干教师”第一名。 第三,我辅导的学生,有上百人在省内外获得各种征文大奖。其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文章十几篇。我的教学论文多次获得省级、全国一等奖。 第四,1993年,我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并获得“人民教师奖章”;1994年,在我32岁的时候,我成为一名特级教师。并作为国家教委和北京市邀请的全国50名优秀教师进京参加第10个教师节大庆。1995年,我又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一等奖。 第五,由于我在语文教育学术方面的新见,1997年,我被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还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并兼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严格说来,我上过三所大学:1981年我毕业于德州师专;198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坐落在孔子之乡的曲阜师范大学本科班,获得正式本科毕业证书和文学学士学位证;而天津教育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授课节目,应当是我的第三所大学! 这所大学,不像那两所那样,发给我正式的毕业文凭、正式的学位证书,他们什么证书也没有发给我。收音机“里面”的教授们,至今,恐怕不知道居然还有我这样一个不在册的学生,我权且把那半尺高的手稿权且当成“文凭”吧! 三所大学的修炼,夯实了我的知识根基,给了我足够的学养,使我能够抱定足够的信念,开始“为师”的远征。 五、读且研:呼唤并构建“新语文教育” 身为语文教师,而我的阅读兴趣和重点,更多在非语文类书籍上。 从走上教师岗位的第一天起,我的阅读触角伸展到文学、文化、哲学类的典籍、报刊上。《读书》《新华文摘》《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等语文教育学科外的杂志,《西方哲学史》《西文现代哲学》,《中国思想史》等书籍,都是我钟爱的。 正是这些阅读,开阔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学术思维,使我能够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对语文教育进行的宏观的思考,使我对愈走愈狭窄,以至拐入死胡同的纯粹工具化的语文教育,有了一定的反思。在僵硬的语文教育理论指导下,语文教育的确有愈来愈背离自身本真、背离汉语教育民族化的趋势。于是,我才有了一系列文章。 1992年,我写作《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在1993年1月的《语文学习》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辽宁朝阳市十五中的王中原老师评价说:“识见高人一筹,宏论振聋发聩”;河南特级教师杜常善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信中称赞拙文是“五四后首篇语文教育新论”。没曾想,我成了中国语文教育界倡导“人文精神”(不是“人文主义”)的第一人。今天,语文教育界,“人文精神”概念及“人文精神教育”,已经几乎人人耳熟能详,而我则是在整整10年前就倡导了这个概念,似乎成了一个“先知先觉”者。 有人误以为,中国语文教育界提出并引入“人文精神”概念,是受了文学界、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影响。这是不对的,语文教育界是在1993年1月份提出“张扬人文精神”,而文学界、文化界是在半年后的1993年6月份,由王晓明教授等人在《上海文学》发表《旷野上的呼唤》一文才提出“人文精神”讨论,文学界、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1993年6月从王晓明教授的此文开始。也就是说,语文教育界提倡“人文精神”,比文学界、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整整早半年。 之后,1999年6月7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长文《反对伪圣化》。针对语文教育中大量存在的师生双方“言不由衷、矫揉造作、说套话、说假话、假崇高、伪神圣”的现象,提出了警惕并反对“伪圣化”的主张。我这篇文章其实早就在网上发表了,而且被广泛转载,甚至被转载到了一家国外的中文论坛上,在那家国外中文论坛上,我的文章后面跟在好几十个海外留学生的帖子。《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我的文章,也颇费了一番踌躇。我早在当年1月份就把文章寄给了他们,可是他们压了半年才刊登出来。因为,19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新闻宣传部门要求报刊媒体,上半年“求稳”,下半年“求热”。我的文章就发在由“求稳”向“求热”转变的关口,“求稳”刚过,“求热”未始。文章发表后,引来的反响我是始料未及的。一位著名教授读到我的文章后,专门给我打来电话,给予我热情洋溢的鼓励。 2000年9月,《语文教学通讯》17期(当时是半月刊)发表了我的《新语文教育论纲》。这篇论文的背景是,轰轰烈烈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热潮即将过去,而中国语文教育究竟向何处去?中国语文教育如何建设、如何发展?一时,在语文教育界内外,还没有人提出系统的前瞻性的理论主张。于是,我就写就了此文,通过此文,我在语文教育界,第一次系统提出并阐述了“新语文教育”的主张。该刊主编桑建中介绍,读者对我的《新语文教育论纲》,反响非常热烈。 早在1996年,我首次提出了“语言的学习的规律,应当是‘举三反一’,而不是‘举一反三’”的主张。语文的学习首先必须“举三”才行,然后才能“反一”。“举三”就是大量阅读、大量积累,这是学习语言的前提。“反一”就是学生自己的读写能力。没有举三,难有反一。这是学习语言、形成言语能力的根本规律。只“举一”不可能“反三”。可是,几十年来,我们中国的语文学习一直偏向“举一反三”。 在《中学语文》(2000年3期)发表《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在《教师之友》(2001年10期)发表《从文以交际、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到文就是道――百年中国语文教育思潮简论》;在《山东教育》(2000年3、4期)连载大约4万余字的《文就是道》;2001年在一系列书刊上连载《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 我的系列论文,有的是从语文教育的外围,宏观地探究语文教育。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思想资源本来本来就稀缺。要宏观把握它的规律,触摸它的历史走向,需要借鉴哲学、文化学、历史学领域的思想资源。我的知识储备与学术思维习惯,对于宏观疏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历史脉络,恰好有益,属于“歪打正着”吧。 一门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常常跳出来,需要一双历史的宏大的“眼睛”。如果在具体学科内里跳不出来,视野就过于狭窄,思路就过于拘囿,那么,就可能造成“门里人看热闹,门外人看门道”的局面。当然,最好的学术目光,是门里与门外结合的“双重目光”。 我之所以那么早就提出“人文精神”,完全是得益于我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走向的密切关注。 而我提出“反对伪圣化”,系统论述“新语文教育”概念,也是借鉴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资源。语文教育理论要走出迷途,要走向深刻,走向朴实,必须借助哲学界的思想资源。 随着我对语文教育的思考的深入,我的语文教育的思想观点,也越来越清晰、越系统。我在一系列报刊上发表了《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也就是收在本文中的《新语文教育的十个原则》)一文,实际上,是具体提出了建设“新语文教育”的10方面的主张,既包涵了我的理论主张,又总结了实践操作。 同时,我又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一个基本原理,向着精神着意,向着语言着力,必然从能力上得益。或者说,着意于精神,着力于语言,必得益于能力。 我所有的重要文章,几乎都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学语文教与学》转载。语文教育应当放弃纯工具性,大力倡导“人文精神”,走向二者融合;师生说话与写作必须大力反对“伪圣化”,言为心声,真朴自然;新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界必须建设为本,共同致力建设“新语文教育”;语文教育的根本规律是“举三反一”以之去弥补“举一反三”,――这些理论主张,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几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共识。假如离开这些理论主张,去描绘、去理解近十几年尤其世纪之交的中国文教育的变迁,那么,至少是不完整的。 如果你登www.google.com网站,输入“伪圣化”一词,那么,你至少会得到7页的信息。“伪圣化”一词已经被中国教育界的越来越多的教师、教育研究者所认同,用它来描绘中国语文教育甚至中国教育中的一种特定的现象。 这些共识的形成,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全体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百年现代语文教育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必须有人来及时概括、及时张扬、及时倡导、及时喊一嗓子。 有人说我是语文教育界的“思想者”,有人说我代表了语文教育的界的自省与反思。我不自量力地说,十几年来,我只不过多多少少就充当了一个概括者、张扬者、倡导者的角色,我做了一个“喊一嗓子”的人。当今,在语文教育界,在文化界,“人文精神”一词,已经几乎人人耳熟能详,新课程标准也已经明确肯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且特别强调要大力倡导“人文精神”,然而,我却是在整整十年前系统提出并大声疾呼的。 我只不过是为“久旱”的中国语文教育引入一丁点儿“思想的甘霖”。 当我的许多观点,常被不少的学术论著、学术论文引用,常被天南地北的数不清的不知名的人的来信与来电称许,那是我最高兴的,比获得什么荣誉称号都由衷欣慰。譬如,河南新蔡练村中学徐中元老师读了我的文章,寄来一个贺年卡,上书:“‘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是一轮冉冉而起的朝阳,让一个上下求索而迷茫的人看到了曙光与方向,于心灵烙下韩老师真心英雄的形象!”。我肯定不是什么“真心英雄”,我只是“真心思索”,我能让全国无数徐老师这样的求索且迷茫的普普通通的老师,感受到现代“新语文教育”的一点曙光与大致方向,我就满足。 更让我感动的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的2000级硕士研究生冯晓云老师,把我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读了我发表的所有论文,写出了关于我学术观点的长篇论文《论韩军的“新语文教育”观》(他的论文附在本书后面)。 六、总概括:我的“新语文教育观” 如果概括我的观点,会看出我的“新语文教育”的一个大致脉络。 新语文教育有“一个本质”。本质上认定,“新语文教育”就是一种“奠基性”的“精神教育”,是通过“语言”奠定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真实自由的个性精神。 “新语文教育”有“两个基本原理”。一、“新语文教育”主张以“举三反一”为主,“举一反三”为辅。二、着意于“精神”,着力于“言语”,必得益于“能力”。 “新语文教育”有“三环节强化语言教学”。一、强化语言揣摩;二、强化大量阅读;三、强化自我习惯。 “新语文教育”有“三个警惕”。一、警惕政治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伪圣化”;二、警惕现代工业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技术化”;三、警惕“后现代”商业文化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萎靡化”。 “新语文教育”有十条原则。:一、重视语言学,更强调文学;二、重视白话,更强调文言;三、重视“举一”,更强调“举三”;四、重视分析,更强调吟悟;五、重视理解,更强调背诵;六、重视散文,更强调诗歌;七、重视崇高与神圣,更强调平实与真诚(反对伪圣);八、重视写实,更强调写虚;九、重视统一,更强调多元;十、重视技能,更强调精神。 七、未刊发:旧手稿中的思想 在整理我这部书稿时,我不能不提及我的未及刊发面世的两篇关于语文教育的论文手稿。这两篇手稿,一直压在我的箱底。大家读了这两篇手稿,可能对于我的语文教育的思想观点,又有个全面的了解。 我今天翻阅这两篇手稿,也感到非常有趣。 此两篇手稿,一篇题目是《限制社会政治语感,张扬人文精神》,一篇题目是《警惕精神“萎靡化”》。这两篇稿子都写在1995年前后。前者,是反思语文教育中的“社会政治形态语感”(或语感的社会政治形态化)现象,后者是忧虑“后现代”的商业文化对语文教育、对教师和学生精神品格的可能冲击。以往,“社会政治形态语感”,曾经从极“左”政治方面消解我们的师生的语言品质,也就是消解我们师生的精神品质;接着,现代工业化的大潮,又从中间角度消解我们师生的语言品质,同样是消解我们师生的精神品质,使师生的精神空壳化;而当今,“后现代”的商业文化,又从极右方面来消解我们的师生的语言品质,同样是消解我们师生的精神品质。前两者,还没有根本铲除,而后者又席卷而来。 这两篇手稿,表明,我对任何侵蚀语文教育的精神本质的现象,都心怀忧虑,都抱有警惕。这两篇手稿还欠圆熟,但收在书里,使我我思想更全面些。 八、心当愧:特级教师须反省 近来我喜欢在网上搜索一些有关“人生四十”的文章,这些帖子或庄重或谐谑,多多少少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已经人过40。我做特级教师马上就满10年。 40岁,难说是身历沧桑。仍有急躁,有狂妄,有幻想,有冲动,但毕竟,沉稳与坦然多了,平静与坚定多了,自信与矜持多了,宽宏与平和多了,胸襟与眼界开阔了,自知之明增长了……我宁愿相信,许多人所说的“人生四十始”,那只是一种浪漫的说法而已。对于我,不是人生能否重新开始的问题,而是自我反省的问题。 我总觉得,作为一个特级教师,一个所谓“名师”,不应当只沾沾自喜地为自己摆功,更应当诚恳反省。我曾在我主持的网络论坛“韩军在线”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特级教师的反省》。 首先,我当为语文教育的低效率而反省。语文教育自设科以来,效率一直不高,目前也不能说效率是高的。语文课所用的时间最多,可是它的效率却一直不理想。我们得问,时间浪费在哪里?特级教师没有责任? 其次,我当为语文教育课程的低欢迎程度而反省。已经不止一次的调查表明,中学生喜欢外语课的程度,高过喜欢母语课。我们得问,语文课怎么了?特级教师没有责任? 再次,我当为在语文课上,让孩子说(写)假话、套话而反省。尽管我写过《反对伪圣化》,但是,我得承认,当学生参加一些关乎他自身命运的语文考试时,我也曾为让学生得高分,违心地让学生写假话、套话。我为此自责。 还应反躬自问:当全社会对语文教育进行大讨论的时候,尽管讨论中有偏激之辞,但,我们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欢迎人家的批评,虚心接受了外界的批评?还是反过来,断然拒绝了外界的批评、甚至想方设法压制了人家的批评?我觉得,如何对待批评,这确实体现的是这个界别的文化气度,这个界别的人的精神涵养! 作为个人,我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惕的地方也有许多,譬如,成了所谓“名师”后,是不是浮躁之气多了,沉静之气少了?是不是有意无意好为人师的时候多了,而谦虚谨慎做学生的时候少了?是不是读书钻研少了,虚与应酬多了?提醒自我警惕。 当今是一个浮躁的社会,人心也难免浮躁,愿学术莫染此气,“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的学术原则,应当不过时吧。 九、仍有梦:做语文课堂艺术家 陆陆续续,我在全国上公开课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不为别的,就为了传布一种“新语文教育”的理念。决不做导师,而是与同行面对面,切磋语文教育的具体的上课方法。 我有一个大的梦想,就是把语文课塑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语文课,当然属于教育范畴,属于在中小学设立的一门以训练听说读写能力为核心的课程。 然而,语文课,却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大家在谈论语文课的时候,只是说,语文课具有艺术的特征,驾驭语文课需要教师具有艺术家的禀赋。但最终,不会承认,中小学的语文课属于艺术范畴,仍然一致认为,语文课,在本质上,属于基础教育领域的一门课程。 我的梦想,是把语文课改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它应该是以引导中小学生鉴赏汉语语言文字之美、提高运用汉语语语言文字的素质为核心。 它应当辅以音乐,或激昂慷慨,或沉缓婉转。把汉语语言文字之美,用音乐烘托出来。 它应当有言语的交锋,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 它应当有幽默,机智穿插,笑声中达情会意。 它应当有朗诵,或男声,或女声,或齐诵,或抑扬,或急缓,把“平面”的语言文字,变成“立体”的交响。 它应当有书法,有图画,有线条,有色彩,传神写照。 课堂是舞台,师生既是角色,师生也是受众,共同演绎一幕“综合的课堂艺术”。 诗经是美的,楚辞是美的,唐诗、宋词、元曲也是美的;文言是美的,白话也是美的;汉语叙事文是美的,汉语议论文、抒怀文都是美的。 语文课堂,为什么不能是美的? 汉语构筑了汉语的文学艺术,我们为什么不能构筑汉语课堂的艺术? 做一个汉语课堂的艺术家,应该不是奢望。 愿全国的语文教师一同构筑一个绚丽的梦,让“新语文教育”,在神州处处开花,使语文教育一片生机。 梦想做“家”,但不做“神”,更不做“伪神”,而做真人。 在最不需要梦想的年龄,梦想依然来临, 在最缺少梦想的年代,梦想依然开花。
十、中年心:走向敬畏与自知
写这些文字时,我40岁;而读者读到它时,我已经41岁。 这两个数字跳入我的眼中,令我惊悚。 多少次,曾经眺望过自己的不惑之年,多少次,遥遥地向往过40岁。 不经意间,40岁已过,41岁已然来临。 曾经想,40岁时,我不会再浅薄,不会再虚妄,不会再鲁莽,不会再无知,我会非常成熟,沉稳,理性,非常富有智慧,学问渊博,知识富有,在某一方面,我会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行家里手。 然而,40岁已经过去,我真实地感到,我依然浅薄、依然虚妄、依然鲁莽、依然无知,这种自我不满的感觉丝毫没有减轻。 实事求是地体察,40岁,我肯定进步了。我虽然没有天天向上,但确实是年年有点滴长进。我不勤奋,但仍算努力;我愚钝,但还是一个正常人。 早在我35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耀眼的光环,近年,主持全国最大的语文教育网络论坛“韩军在线”,担任《中国青年报》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委,等等。 之所以感到自己依然浅薄、依然虚妄、依然鲁莽、依然无知,是因为,人对完善、成熟、渊博、智慧的追求……,是绝对性的,是无止境的;是内在的沉实、宁静,不是外在的浮华、喧嚣。 这种向往与追求,本然地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它是游移的、不断增量的。向往与追求本身,是一种永恒持久的心态。生命无止境,境界无尽头。 我总觉得,人的成长,不是一个正向过程,而是一个逆向过程。成长,不是使人愈来愈胆大,而是使人愈来愈胆怯。成长,不是使人愈来愈沉醉于自我的所谓辉煌,而是使人愈来愈发现自我缺陷、自我瑕疵、自身的毒疮。 成长,映射在心灵上,不是心灵愈来愈膨胀,而是愈来愈收缩;不是愈来愈胆壮气盛,而是愈来愈胆怯气虚;不是愈来愈自大,而是愈来愈自知。 这种感觉无以名之,姑且叫作“敬畏”吧。 世间人与事,许许多多,纷纷纭纭,不少使我产生由衷的敬畏。 我敬畏学生。有时,学生突然提出问题,我无以应对,对后生的敬畏,油然而生。 我敬畏前辈。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前辈关于母语教育的见地,已鞭辟入里,经验已十分成熟,而后生却还在绕弯子,争来吵去,玩弄名词术语,实在遗憾。 我敬畏“外行人”。在有些“外行人”看来,语文教育十分简单,十分朴素,本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东西,有时,“外行人”三言两语,就点中语文教育的“命门”,令我茅塞顿开。我由衷敬畏他们。 我敬畏身边的每个人。他可能是勤勉的民工,可能是纯真的婴儿,可能是平和深沉、不事张扬的老人。他们都在向我诠释一种人生态度。 我敬畏大自然。它可能是默默生长的花草,可能是静静矗卧的山川,可能是无语的斜阳,可能是清亮的鸟鸣。它们都在为我树立一种灵魂姿态。 40岁,心灵走向敬畏,应不是衰退吧。 曾有四句“打油”:淡泊恬静朴为本,平平淡淡拙是真。滴泪泣血说语文,从容练达做韩军。  |